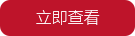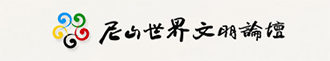尼山會客廳 | 姚海濤:荀學的研究路徑與思政育人實踐
2025-11-21 10:42:13 來源:中國孔子網 作者:解放
編者按:
為持續推動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本色建設,系統推進新時代儒家思想研究闡發,中國孔子網特別推出《尼山會客廳》訪談專欄,邀請專家學者,解讀儒家思想的智慧精髓,深入剖析儒家思想的時代內涵與當代價值,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搭建學術交流平臺。近日,中國孔子網采訪青島城市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姚海濤,圍繞荀學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中國孔子網:您從法學學士到哲學碩士的學業進階中,是什么契機讓您將先秦儒家哲學尤其是荀子思想作為核心研究方向?
姚海濤:考研從法學跨越到哲學,雖同是在文科大類中流轉,但對于當時沒有哲學課程背景的我來說,這一學業進階的難度很大。《西方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史》這兩門專業課成為橫亙在面前的兩座大山。哲學是智慧之學,對理解能力要求極高。當時我因是跨專業考研,想憑閱讀指定的參考書搞懂弄通中西方哲學,無異于天方夜譚。恰好同年級另一個專業正在開這兩門課。于是我就旁聽了陸茵老師的《西方哲學史》和林永光老師的《中國哲學史》。就這樣,我順利地進入山大中國哲學專業讀書,以儒家哲學為研究方向,得以親炙諸位恩師,走進學術,親近儒家。現在想來,將荀子思想作為核心研究方向的契機生發于讀書期間。
契機之一,授業恩師苗潤田先生和劉蔚華先生合著的《稷下學史》對我的影響。此書是稷下學研究的重要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拓荒意義。恩師從事稷下研究,學生自然不能不有所涉獵。若研究稷下學,《稷下學史》自然是案頭書。而稷下學研究,荀子是當然的重鎮。稷下學宮是百家爭鳴的最主要舞臺,而荀子曾于此“三為祭酒”“最為老師”,成就了自身百家爭鳴時代學術領袖和諸子百家集大成者的崇高地位。荀子有其他先秦思想家不具備的一些標識性特征,比如批判性思考、熔鑄性建構和系統性寫作。流傳至今的《荀子》可視為批判熔鑄品格的佳作,多是獨立成篇的系統論文。
契機之二,顏炳罡先生當時為我們研究生開了《荀子導讀》課。這門課程是我聚焦荀子研究的關鍵一環。記得《荀子導讀》課,當時沒有固定教材,我們去圖書館借,所以上課用的《荀子》版本五花八門。同學們從洪家樓校區圖書館借的多是197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詩同的《荀子簡注》。顏老師用的則是北大注釋組197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荀子新注》。當年《荀子導讀》的課堂筆記,記錄了顏老師帶領我們研讀《荀子》的軌跡,我保留至今。可以說,這課程為我埋下了研究荀子的種子,如今《荀子》仍陪著我一直往前走。
契機之三,荀子當時并未成為學術研究的顯學,因此有巨大的研究潛力。一般而言,學術研究注重研究熱門人物及其思想,但熱門人物往往因研究者眾多,難以有突破性成果。而當我開始研究荀子之時,荀子在學界的地位正如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樣,遠未成為“中心”式的人物,正好可以作為深耕的研究領域。可以說,在眾多契機的共同湊泊之下,荀子思想成為了我的核心研究方向。
中國孔子網:您提出用“三分法”詮釋荀子人性論,還系統梳理了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的“批判汲取與熔鑄反哺”作用,這些創新視角是如何形成和完善的?
姚海濤:一言以蔽之,這些研究視角形成于長期耕耘荀子研究過程之中,是受到眾多學界前輩研究啟發的結果。
荀子人性論是學界多年以來的研究熱點,出現了性可善可惡論、善偽論、弱性善論、性樸論、性趨惡論等等不一而足的觀點。羅爾斯曾有一段關于如何讀書的自白,頗足發人深省。他說:“我讀前人的著作,如休謨或康德,有一個視為當然的假定,即這些作者比我聰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費自己和學生的時間去研讀他們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爾在他們的論證中見到了一點錯誤,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他們自己一定早已見到了這個錯誤,并且處理過了。總之,他們的著作中絕沒有簡單的一般錯誤,也沒有關系重大的錯誤。”荀子的人性論亦當如是觀,因此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釋是學界責無旁貸的責任。
三分法作為與二分法并立的哲學研究范式,引入荀子及其人性論研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我對“三分法”引入荀子人性論研究進行了合法性研判。黑格爾辯證法所論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一式”最廣為世人所知,是為三分法之典范模式。中國哲學三分法更是源遠流長,對“三”之重視比比皆是。龐樸先生的《中庸與三分》一文指出:“世界本來便是三分的。”這一從中國哲學自身發展理路中找到了作為解釋世界的“三分”,具有普適性指導意義。楊澤波先生在對孔子思想結構的分析中也提出了三分法:“所謂三分法,就是將與道德相關的因素劃分為智性、仁性、欲性三個部分,以區別于西方理性、感性兩分格局的一種方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以三分法詮釋荀子人性論建基于中西哲學研究范式之不同的基礎之上,受到前人研究成果的啟發,以及近年來人性論研究困境的刺激而得出的研究視角轉變。
三分法視域中的荀子人性論有兩大維度:縱向的時間歷史維度與橫向的學理邏輯維度。其一,從縱向的時間歷史維度看,三分法能夠完整地再現從漢唐、宋明至清代的荀子人性論認知史,即基本肯定、全面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三個連續交織的思想史階段。其二,從橫向的學理邏輯維度看,三分法可將荀子人性分為欲惡之性、辨知之性、積偽之性三個連續上升的哲理蘊謂層次。
作為生長于齊魯大地的學人,自然對齊魯文化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齊魯文化有悠久的歷史,是自西周分封之后形成了格調迥異而互補的文化。齊魯文化有一個合流的過程,最終形成了不分你我的齊魯文化。伴隨著儒學定于一尊,齊魯文化遂由一種地域性文化而躍升為中華文化之主流。這是其他地域文化所無法相比的。荀子雖是趙人,但其學術與政治均在齊魯之地展開,其生命定格于蘭陵。在探索過程中,我發現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過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16年我立項了一個課題“文化批判與理論熔鑄——齊魯文化合流中荀子的關鍵作用研究”,借此課題展開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此課題結題后,關于這個問題的思考并沒有結束。這一課題的研究與表述當時并不成熟,且有不太恰當之處,于是我又進一步將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的作用修正為“批判汲取與熔鑄反哺”。
中國孔子網:您之前深入研究過荀子對數術的系統批判,還形成了自己的獨到觀點,能否分享這項研究從選題構思、文獻梳理到論證深化的完整過程?您是如何突破數術研究中史料零散難題的?
姚海濤:荀子對數術的系統批判這項研究是我在研究荀子思想近十年之后的2018年開始構思。因為有前期對荀子的深度研討,形成了對荀子文本與學術品格的基本把握,連帶著對戰國數術之學的背景有了一定的認識。而要將二者結合起來,需要一個觸發契機。
荀子對數術雖沒有專門立論批評,但檢視《荀子》一書,可抽繹出其對數術傳統的系統批判。系統批判的框架受到李零先生將數術系統分為占卜、相術、厭劾祠禳三大部類的啟發。此外,丁山先生的《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劉大鈞先生的《周易概論》、朱伯崑先生的《易學哲學史》、胡新生先生的《中國古代巫術》、李零先生的《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陳來先生的《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和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等對于此項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這一研究成果的面世還要感謝《周易研究》雜志及外審專家。論文寫畢投稿后,外審專家給出了“該文選題具有較好的學術性與一定的創新性”的正面評價,還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見,比如指出了論文結構欠合理、論證薄弱、學術史背景弱等問題。經過多輪的反復打磨與外審之后,終于獲得發表。這一過程對于個人學術發展來說,是一次錘打與歷練。這讓我對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提出的“人生三境界”有了切己的體認,從“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迷茫到“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堅持,再到“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頓悟,確實讓人有一種脫胎換骨之感。經過這次磨礪,自己在研究上可以說上了一個臺階。后來這一研究還獲得了青島市第三十六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數術研究中史料零散可能主要對于整部數術史的研究而言是重大難題,由于我聚焦于荀子對數術之批判,因此只需要注意戰國之時的數術史實即可。而對于這一階段的數術史研究,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我需要做的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式的選擇,貫注以問題意識與縝密思考,得出確切的結論而已。因此這一研究雖非原始創新,卻屬于交叉式、接力式的拓展研究,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才有一點新的認識罷了。
中國孔子網:作為“山東學校優秀思政課教師”,您在教學實踐中,如何將荀子哲學、齊魯文化等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思政課堂的教學資源,實現學術研究與思政教育的有機融合?
姚海濤: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山東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明了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后來提出的?“兩個結合”重要思想,尤其是“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為我國文化、教育各項事業發展,為山東從文化資源大省向文化強省邁進,為學者從事文化研究均能提供重要指導。
挖掘地方文化資源,賦能思政課建設,服務于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是思政課教師的職責所在。作為一所山東省內的大學,傳播齊魯文化,以豐厚的齊魯文化資源育人這是山東教育、山東思政教育的應有之義。
學術研究與思政教育的融合是對一名思政教師的基本要求,也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一般來說,學術反哺教學有三個維度。一是,學術成果的直接輸出,即將學術研究成果傳播到課堂與學生中去。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直接的維度,因為學生并未有相關領域內學者那樣的學術背景,不會有太強烈的共鳴,因此效果往往不會太理想。二是,學術方法的傳遞,即將學術研究的方法教授給學生。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無論是對老師還是學生都有很高的要求。需要教師凝練學術方法,亦需要學生具備將方法遷移并轉化到專業學習中的能力。三是,學術成果的間接輸出,即將學術研究成果經過通俗化、大眾化的改造之后再進行傳播。這對教師的要求可能就更高了,需要教師“接地氣”,具備相當的轉化能力與表達能力,甚至需要個人魅力。
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思政課堂的教學資源方面,齊魯文化(包括荀子哲學)中的人性觀點、禮法觀念、修身理論、哲學思想等無一不可以融入課堂教學和教育全過程。概括地講,要建立“一體兩翼,三個抓手”的教學體系,即以思政課的教學目標(立德樹人)為主體,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齊魯文化(包括荀子哲學)等為代表的學術研究成果為兩翼,以知識點滴灌、專題探究、實踐體認為三抓手,實現從理論灌輸向文化浸潤轉變,從知識傳授向價值引領轉變,從被動接受向主動探究轉變。
道理雖是如此,但知易行難,正如荀子所言:“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
中國孔子網:您在推動齊魯文化創新研究,在學術成果大眾化傳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您認為在新媒體時代,傳統儒學思想的傳播應把握哪些關鍵點?
姚海濤:新媒體時代的來臨打開了齊魯文化傳播機遇與挑戰并存、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并存的新局面。研究與傳播是車之兩輪,不可或缺。研究難,傳播亦不易。研究面對的對象是文本與思想,而傳播面對的則是觀眾與媒體。習近平總書記曾有“把論文寫在田野大地上”的重要論述。這一論述啟示傳統儒學思想的傳播,除了將論文寫在期刊雜志上,更要將儒學播灑在網絡世界中,散布于新媒體上。
新媒體時代傳播傳統儒學思想與前一問題中的學術研究與思政教育有一定的關聯性與一致性。思政教育面對的主要是學生,而新媒體時代傳播儒學面對的受眾是各個年齡、不同職業的普羅大眾,因此難度可能會更大。儒學是關于人的學問,是普適性的學問,因此新媒體這一關要過。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一個關系到儒學的現代生命力及其延續的大問題。
儒學傳播要處理好守正與創新的關系,處理好古與今的關系。儒學之為儒學的永恒性、普適性的內核即是守正,而儒學的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的特性即是創新。與此同時,儒學是有用之學,有修身養性、治國理政之用,這一層面就需要貫通古今的廣闊視野,以達到以古鑒今之目的。
儒學傳播要做到社會全覆蓋,需要做好線上、線下兩篇大文章。線上方面,可喜的是,如今各個網絡平臺上,有不少儒學傳播者,堪憂的是,水平參差不齊。尤其讓人欣喜的是,出于正本清源的需要,不少儒學研究者從講臺走到了網上,擔負起了儒學傳播守正創新的重任。比如鮑鵬山老師的短視頻非常好,能夠點醒聽眾,廓清很多歷史謎題與現實困惑,讓聽眾在儒學真精神的引領下實現“成人”。線下方面,廣大的農村和城市社區均需要儒學浸潤。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更加多樣。儒學成為當今人們文化生活的重要構成。比如顏炳罡老師的鄉村儒學、社區儒學已經成為文化“兩創”的省級標桿甚至國家級典型案例,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儒學傳播要達到好的效果,需要實現話語體系、呈現形式和傳播場景的三大轉化。話語體系的轉化,即從學術語言到生活語言。呈現形式的轉化,即從文字為主到視聽融合。傳播場景的轉化,即從課堂講堂到社交平臺。
此外,儒學傳播還要警惕“兩個誤區”:娛樂化與碎片化。
避免“娛樂化”走向“庸俗化”。運用輕松的形式不等于放棄深刻的內核。要防止為了流量而將儒學思想庸俗化、淺薄化,甚至曲解。必須在“有趣”和“有料”之間找到平衡,做到內涵與形式的統一,讓聽眾雅俗共賞,真正對個體與群體的生活有所助益。
避免“碎片化”割裂“系統化”。新媒體傳播天然具有碎片化特征,但儒學是一個有機的思想體系。因此,在制作碎片化內容的同時,要通過系列化策劃、主題化整合、知識鏈接等方式,為受眾構建一個隱形的“認知地圖”,讓他們在點滴收獲中,最終能拼湊出對儒學精神相對完整的理解。
總體而言,新媒體時代的儒學傳播,本質上是一場深刻的“翻譯”與“連接”工作。它要求我們既要做經典的“守正者”,準確把握其精神實質;又要做創新的“弄潮兒”,熟練運用新媒體的邏輯與工具,讓古老的智慧在當代人的心田中,重新生根發芽,煥發出蓬勃的生命力。
中國孔子網:作為青島城市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您認為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與傳統儒學研究交叉融合?
姚海濤:我所在的高校目前未設立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與專業,工作重心主要圍繞公共課與思政課教學展開,同時輔以一定的研究工作。基于這一實際情況,我主要從課程建設與學術研究兩個方面,談以下三點認識。
第一,處理好“經典互釋”與“價值貫通”的關系,推動思政課教學內容與經典理論的有機融合。在相關課程中,深入闡釋“第二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邏輯內涵與時代意義;將儒家思想中的“誠信”“仁愛”“孝悌”等觀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誠信”“友善”“和諧”等價值進行對照講解;推動荀子“禮法”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法治觀展開理論對話,增強學生的理論認同與文化自信。
第二,處理好“理論教學”與“實踐育人”的關系,加強思政課實踐教學中的研學設計與實施。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推動文化育人與實踐育人協同并進,實現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發展雙向促進。
第三,處理好“守正創新”與“互鑒融通”的關系,推進學術研究在融合中實現發展。以“第二個結合”為指引,致力于推動傳統儒學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為相關理論探索貢獻一份力量。
【編輯:董麗娜】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