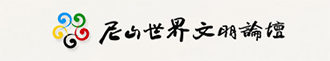海昏侯《詩經(jīng)》簡為什么重要
2025-11-21 09:25:58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于浩
 ?
?
海昏侯《詩經(jīng)》簡目錄部分,右為整簡,左、中為局部放大。資料圖片

海昏侯墓出土《詩經(jīng)》簡,右為全簡,左為局部放大。此簡為目錄首簡,內(nèi)容是:詩三百五扁(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資料圖片
2015年海昏侯墓的考古發(fā)掘曾引起轟動,在海昏侯墓考古發(fā)掘成果公布10周年之際,海昏侯墓的一些重要發(fā)現(xiàn)再一次成為公眾聚焦的熱點。除了炫目的金餅、褭蹏金、麟趾金,精美絕倫的青銅當盧,迄今為止出土密度最高的漢代漆紗以及嘆為觀止的漆器、玉器、銅器等等之外,海昏侯墓出土的簡牘也成為討論中心。根據(jù)湖北省荊州文物保護中心主任方北松公布的最新數(shù)據(jù),海昏侯墓出土的簡牘一共有5795枚。從出土文獻來看,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shù)字,何況這些竹簡中有大家耳熟能詳?shù)牡浼骸墩撜Z》《孝經(jīng)》《春秋》《大戴禮記·保傅》……當然,還有《詩經(jīng)》。這些竹簡不僅給我們展現(xiàn)了海昏侯劉賀的知識世界,也使得西漢時期的儒學(xué)發(fā)展面貌直觀地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
這些竹簡中,《詩經(jīng)》簡達1200多枚,遠超此前所有類似的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清洗、拍攝紅外照片、釋讀等工作,北京大學(xué)教授朱鳳瀚于2020年公布了初步整理材料,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成為后來學(xué)界討論的基礎(chǔ)。公布材料顯示,海昏侯《詩經(jīng)》簡由目錄、正文構(gòu)成,每簡有3道編繩、容字20~25字。竹簡殘損嚴重,給整理帶來了很大難度。但無論如何,海昏侯《詩經(jīng)》簡都是目前存簡數(shù)量最多、信息量最大的出土《詩經(jīng)》文本。
海昏侯《詩經(jīng)》簡有什么不一樣
近50年來,出土《詩經(jīng)》類文獻層出不窮,引發(fā)學(xué)界持續(xù)討論,其中與傳世《詩經(jīng)》文本相關(guān)的,除海昏侯《詩經(jīng)》簡外還有4種: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出土漢簡《詩經(jīng)》(簡稱阜陽漢簡《詩經(jīng)》)、2015年安徽大學(xué)搶救入藏的戰(zhàn)國楚簡《詩經(jīng)》(簡稱安大簡《詩經(jīng)》)、2015年湖北荊州夏家臺106號楚墓出土戰(zhàn)國楚簡《詩經(jīng)·邶風》簡、2021年湖北荊州王家嘴798號楚墓出土戰(zhàn)國楚簡《詩經(jīng)》(簡稱王家嘴楚簡《詩經(jīng)》)。雖然近年來出土文獻屢有新發(fā)現(xiàn),大有“地不愛寶”之勢,但是絕大多數(shù)還是殘編斷簡,發(fā)現(xiàn)傳世典籍更是不易,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前述4種出土的戰(zhàn)國與漢代《詩經(jīng)》簡相當重要,當年阜陽漢簡公布時,亦引起了很多討論,至今仍有進一步研究和參考價值。
與前述4種出土《詩經(jīng)》簡相比較,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學(xué)術(shù)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從出土竹簡數(shù)量上來看,阜陽漢簡《詩經(jīng)》存簡170多枚,而且?guī)谉o完簡,安大簡《詩經(jīng)》存簡93枚,夏家臺出土的總共400多枚楚簡中,目前公布的《詩經(jīng)》簡只有《邶風·柏舟》,王家嘴楚簡《詩經(jīng)》有300多枚,而海昏侯《詩經(jīng)》簡多達1200多枚,遠超此前所有發(fā)現(xiàn)。其次,安大簡、夏家臺楚簡、王家嘴楚簡《詩經(jīng)》都只有國風部分,沒有小雅、大雅、三頌部分;阜陽漢簡《詩經(jīng)》絕大部分是國風,小雅只存《鹿鳴》《伐木》兩篇,其余雅頌部分也付之闕如。而海昏侯《詩經(jīng)》簡國風、小雅、大雅、頌首尾完具,雖因時代久遠,又經(jīng)長時間浸泡、擠壓,竹簡殘破得較為厲害,但海昏侯《詩經(jīng)》簡仍然是目前最為完整的出土《詩經(jīng)》文本。更為重要的是,海昏侯《詩經(jīng)》簡還有目錄,正文中有注釋,部分詩篇最后有類似于詩序的“題旨概括語”,這樣豐富的內(nèi)容也是以往出土《詩經(jīng)》文獻所未見。阜陽漢簡《詩經(jīng)》有3片類似于序的殘簡,有“風(諷)君”“后妃獻”等字樣,因殘損嚴重,面貌不清晰。海昏侯《詩經(jīng)》簡則多篇詩末有題旨概括語,寫在記錄句數(shù)、章數(shù)和總章句數(shù)文字下,體例較為統(tǒng)一。
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目錄置于竹簡的前端,格式按國風、雅、頌三部分分類排列,記錄了海昏侯《詩經(jīng)》總篇、章、句數(shù)。目錄按照詩的每一章第一句來進行登記,還會寫明每一章有多少句,這讓我們不僅能知道詩篇排列的次序,還能知道每首詩內(nèi)部每章的排列次序。而目錄顯示,海昏侯《詩經(jīng)》的部分篇次、章次與今本《毛詩》次序不一樣,這證實了相關(guān)史料中漢代“三家詩”部分篇次與《毛詩》有異的記載。近代以來,不少學(xué)者嘗試通過歷代殘存的熹平石經(jīng)《魯詩》拓片和歷次出土的熹平殘石還原《魯詩》部分篇次,并由此發(fā)現(xiàn)《魯詩》的大雅部分和小雅部分,有不少詩篇次序和《毛詩》不同。海昏侯《詩經(jīng)》的目錄顯示它的大雅篇次、小雅篇次與熹平《魯詩》篇次完全一致,不僅證實了學(xué)者們還原的準確性,也透露出海昏侯《詩經(jīng)》很可能與失傳已久的《魯詩》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海昏侯《詩經(jīng)》內(nèi)文的體例,是各詩的每一章下注明章次和句數(shù),注釋則在相應(yīng)詩句后,屬典型的“隨文釋訓(xùn)”。比如《小雅·祈父》的第二章,簡文是這樣的:“祈斧(父),予王之蚤(爪)士,胡轉(zhuǎn)予于(恤),靡所底(厎)止。底,猶止也。其二四句”(按: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括號內(nèi)為今本文字)。簡末的“其二”,表示這是《祈父》的第二章,“四句”,表示這一章是4句。熹平石經(jīng)《魯詩》也會這樣標示章次,只是沒有記句數(shù)的文字。“底,猶止也”,就是訓(xùn)詁,解釋“底”字的意思。目前來看,雖然海昏侯《詩經(jīng)》這類訓(xùn)詁整體數(shù)量上比《毛詩故訓(xùn)傳》要少,但前后體例嚴謹,加上不僅有訓(xùn)詁,而且有序,說明海昏侯《詩經(jīng)》很可能不是簡單的《詩經(jīng)》文本,而是一部西漢時期的《詩經(jīng)》著作。西漢經(jīng)學(xué)著作保存下來的就屬吉光片羽,據(jù)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西漢《詩經(jīng)》著作一共12部(實際上應(yīng)不止此數(shù),比如楚元王劉交也曾編次詩傳,稱作《元王詩》,可能在西漢末就失傳了),這12部著作,留存下來的僅有兩種,即《毛詩故訓(xùn)傳》和《韓詩外傳》,且《韓詩外傳》很可能經(jīng)過了后人的增益,《魯詩》《齊詩》則相繼亡佚。海昏侯《詩經(jīng)》的出土,意味著失傳已久的西漢《詩經(jīng)》著作重新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意義重大。
隨著戰(zhàn)國秦漢時期學(xué)術(shù)發(fā)展,在儒家經(jīng)典的解釋、詮說方面逐漸出現(xiàn)了傳、說、記、故、訓(xùn)等多種體式,傳后來又有內(nèi)傳、外傳之體。現(xiàn)存的《毛詩故訓(xùn)傳》是“故訓(xùn)”與“傳”合一的體例,也是隨文釋訓(xùn),目前看來,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體例與《毛詩故訓(xùn)傳》最為接近。《韓詩外傳》是外傳之體,但可能書里也有部分內(nèi)傳。前人對于這些體式有很多討論,海昏侯《詩經(jīng)》的出土,無疑對進一步深入研究西漢經(jīng)學(xué)解釋體式有很大的幫助,對理解《毛詩故訓(xùn)傳》的體例及產(chǎn)生時代等問題也有助益。《漢書·藝文志》里記載的魯詩著作有《魯說》《魯故》,它們的體例和特點究竟如何,海昏侯《詩經(jīng)》簡也能提供不少思路。至于海昏侯《詩經(jīng)》簡是否為《魯故》或《漢書·藝文志》里的其他著作,則有待材料全部公布再做深入討論。
還原西漢學(xué)術(shù)“活態(tài)”場景
海昏侯劉賀去世于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包括《詩經(jīng)》簡在內(nèi)隨他下葬書籍的抄寫時間肯定在此之前,根據(jù)史料記載和海昏侯墓其他陪葬品的情況,這些書籍很可能在劉賀還是昌邑王時期就已存在,因此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成書時間可能為武帝末年昭帝初年,或昭帝時期至宣帝初年。西漢學(xué)術(shù)史上,有兩次標志性的歷史事件,對經(jīng)學(xué)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一次是漢武帝建元年間立五經(jīng)博士,一次是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開石渠閣會議。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確立了漢代的經(jīng)學(xué)制度,也確立了官方認定的《詩經(jīng)》學(xué)為“魯詩”“齊詩”與“韓詩”三家(也有學(xué)者認為武帝時期只確立了“魯詩”)。石渠閣會議則將五經(jīng)博士增至12員,奠定了兩漢經(jīng)學(xué)主要格局。海昏侯《詩經(jīng)》簡正好處在這兩個重要時期的中間時段,給研究西漢經(jīng)學(xué)發(fā)展提供了可以參照的實例。并且,劉賀身邊不少學(xué)者正是西漢《詩經(jīng)》學(xué)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我們借由海昏侯《詩經(jīng)》簡,可以還原西漢學(xué)術(shù)“當時”與“在場”的活態(tài)場景。
《詩經(jīng)》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已編定成書。秦始皇焚書,非官方所藏書不得收藏、討論、研究,只能靠記誦得以傳承,這個被稱為“挾書律”的禁律,直到漢惠帝四年才廢除,此后一大批經(jīng)典古書逐漸公開傳播并被抄寫成文本,《詩經(jīng)》大概也是這時期被重新抄寫下來的。當時《詩經(jīng)》有多個傳人,較早是魯人申培,他與劉邦同父異母之弟劉交同受《詩》學(xué)于荀子門人浮丘伯,劉交后來被封為楚元王,派遣其子劉郢客與申培繼續(xù)在浮丘伯門下學(xué)《詩》,申培傳下來的《詩》后來稱為“魯詩”,他弟子眾多,是漢代最為興盛的《詩經(jīng)》流派。其次是齊人轅固生,為人剛直,漢武帝征召他時他已經(jīng)90多歲,他傳下來的就是“齊詩”,在漢代影響力僅次于“魯詩”。另有燕人韓嬰,漢文帝時期曾擔任博士,精于《易》學(xué)和《詩》學(xué),他所傳即為“韓詩”。這三家在漢武帝時期都被立為學(xué)官,并稱為“三家詩”。此外,魯人毛亨傳承《詩經(jīng)》,傳授給弟子趙人毛萇,就是“毛詩”。毛萇為河間獻王劉德(漢景帝之子)的博士,“毛詩”沒有被武帝立為官學(xué),只是作為一種地區(qū)性的學(xué)派在傳授。但東漢時期,“毛詩”逐漸興盛,東漢末年大儒鄭玄以《毛詩故訓(xùn)傳》為本給《詩經(jīng)》作箋,雜糅齊魯韓三家之說,稱《毛詩傳箋》,流行甚廣,“三家詩”遂漸漸不傳。四家《詩》學(xué)本來都有各自的《詩經(jīng)》文本和著作,漢末魏晉時期,“齊詩”“魯詩”先后失傳,“韓詩”文本也失傳,只剩下《韓詩外傳》。流傳至今的《詩經(jīng)》文本,其實就是“毛詩”一家的文本。
“魯詩”由許生和徐公傳給王式,王式曾擔任昌邑王傅,也就是劉賀的老師。“韓詩”由韓嬰傳給他的后人韓生,韓生傳給趙子,趙子傳給蔡誼,蔡誼傳給食子公和王吉,王吉曾擔任昌邑中尉。這兩位在《詩經(jīng)》傳承上非常重要的學(xué)者都與劉賀有密切的關(guān)系。劉賀還是昌邑王時,喜駕車馳騁于國中,王吉用《檜風·匪風》和《召南·甘棠》兩首詩來勸諫劉賀。王式也曾用《詩經(jīng)》來勸諫劉賀,當劉賀被廢后,治事使者責問王式說:“師何以亡諫書?”王式回答:“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fù)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漢書·儒林傳》)這是漢代經(jīng)學(xué)史上一句很著名的話。
另一位以明經(jīng)著稱的學(xué)者龔遂擔任昌邑郎中令,他曾對劉賀說:“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意思是大王您誦讀《詩經(jīng)》三百零五篇,應(yīng)該通徹人事、了解王道,現(xiàn)在您所行符合《詩》里的哪一條啊!劉賀即位后,夢見宮中西階東堆積著大量的青蠅之屎,后來果然在宮殿覆瓦下面發(fā)現(xiàn)了不少,龔遂就對劉賀說:“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cè)讒人眾多,如是青蠅惡矣。”(《漢書·武五子傳》)這里龔遂提到“陛下之《詩》”,也就意味著劉賀身邊應(yīng)該有《詩經(jīng)》文本。如今劉賀的墓中就發(fā)現(xiàn)了一部《詩經(jīng)》,很可能就是龔遂說的“陛下之《詩》”。從王式、王吉、龔遂3人的身份來看,王式是劉賀的老師,有輔佐、勸諫、教導(dǎo)之責,加上他自己說“以三百五篇諫”,因此這個“陛下之《詩》”很可能就是王式用來教導(dǎo)、勸諫劉賀的文本。劉賀即位27日即被廢黜,他從昌邑帶過來的屬臣幾乎全部被誅殺,但王式、王吉、龔遂因為屢次用《詩經(jīng)》來勸諫劉賀而得以幸存。王式后來居家教授《詩經(jīng)》,他的傳人唐長賓、張長安、褚少孫都有建樹,因此王式成為西漢時期“魯詩”承上啟下的關(guān)鍵人物。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發(fā)現(xiàn),使這一段學(xué)術(shù)史有了實物的證據(jù),它當中所透露的信息也將更好地還原學(xué)術(shù)“活態(tài)”場景,怎能不令人激動。
《詩序》研究有了參照物
《詩序》問題是《詩經(jīng)》學(xué)史上最核心,也是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因為保存至今的《毛詩序》不僅是中國詩學(xué)理論最早也最為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對每首詩背景、主旨的解釋也成為后來理解《詩經(jīng)》的基礎(chǔ),后人不論是贊同還是反對,都要根據(jù)《毛詩序》發(fā)言。但是它的時代、作者等問題卻聚訟紛紜。從《四庫全書總目》中可以總結(jié)出至少11種觀點,大體上這些觀點可分為4類:一是認為它是子夏所作;二是認為子夏先創(chuàng),后人增益,這個后人可能是毛公、東漢衛(wèi)宏、漢代其他學(xué)者等;三是認為國史所作;四是認為《毛傳》之后的學(xué)者所作。第三、四類觀點,多是唐代、宋代學(xué)者提出的,而漢代學(xué)者多認為《毛詩序》為子夏所作,或至少是子夏所傳。至于出現(xiàn)東漢人所作之說,主要是因為范曄《后漢書》里記載東漢學(xué)者衛(wèi)宏作《毛詩序》,所以近代學(xué)者多以此為根據(jù),認為《毛詩序》為衛(wèi)宏所作,否定其價值。不過近年來經(jīng)過一些學(xué)者詳細考證,衛(wèi)宏所作的應(yīng)該是《毛詩序注》,衛(wèi)宏作序說漸漸被排除。
《毛詩序》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總結(jié)詩的起源、功能、意義等的《詩大序》,一個是列在每首詩前面、用來解釋詩篇題旨背景等的小序。解釋題旨、背景的小序又被古代學(xué)者分為“首序”(或稱“序首句”)和“續(xù)序”(或稱“續(xù)申之詞”)。因為古代學(xué)者發(fā)現(xiàn)序的第一句和后面的話似乎不是一人一時所作,后面的續(xù)序往往像是在解釋序首句,所以宋代學(xué)者認為序首句來源比較古老,可能是子夏所傳,續(xù)序則是漢代“毛詩”學(xué)者增益的。除了《毛詩序》的問題以外,“三家詩”有沒有序也是討論的重點。比如清代學(xué)者從紛繁復(fù)雜的傳世文獻中鉤沉出了不少“三家詩”的序,提出“三家詩”也應(yīng)該有序的觀點。
這些問題,因為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出現(xiàn),有了新的、更重要的參照物,那就是海昏侯《詩經(jīng)》簡中的“題旨概括語”,我認為這就是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序”。這個序不僅證實了西漢“三家詩”確實有序,也可以給《毛詩序》的時代問題、形成過程帶來新的啟示。
首先,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序都特別簡潔,以2到5字來概括一首詩的題旨,如《周南·桃夭》題為“說人”(“說”通“悅”),《檜風·匪風》題為“刺上”,《大雅·既醉》題為“直言”,等等。這與傳世文獻里鉤沉出的“三家詩”序幾乎完全一致,比如《文選》李善注里引用到的韓詩序有“《漢廣》,悅?cè)艘病保啊段[蝀》,刺奔女也”,等等。古代學(xué)者說“三家詩”有詩序,應(yīng)該是沒有問題的。
其次,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序都寫在每首詩的末尾,在記錄篇名、章數(shù)、句數(shù)和總章句數(shù)的后面。這種記錄形式值得特別注意,書寫出來是這樣的:“《庭燎》,三章章五句凡十五句,□(追)道。”因為東漢學(xué)者蔡邕所撰《獨斷·宗廟所歌詩之別名》保存有周頌各篇的解釋,過去學(xué)者認為很可能是遺留的《魯詩》序,內(nèi)容是:“《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惟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從形式上看與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記錄方式幾乎一模一樣。可見蔡邕很可能是直接從《魯詩》文本上抄下來的。目前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周頌各篇還沒有公布,公布之后如果基本相同,就可以證明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序和蔡邕《獨斷·宗廟所歌詩之別名》都是《魯詩》序;如果有不小的差異,則要進一步討論《魯詩》序有沒有增益和修改的可能。
再次,《毛詩序》的首句也非常簡略,也是用一句簡短的話來概括題旨,這就引發(fā)我們的思考:它是不是與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序有著同樣的性質(zhì)。根據(jù)傳世文獻中散存下來的“三家詩”序和海昏侯《詩經(jīng)》序來看,這應(yīng)該是西漢經(jīng)師解釋《詩經(jīng)》題旨的主要方式,想必“毛詩”也是如此。這樣一來,《毛詩序》的作者就不可能是子夏,它產(chǎn)生的時代應(yīng)該是西漢早期。同時,它的續(xù)序也應(yīng)該是西漢時期的“毛詩”后學(xué)所增,《毛詩序》應(yīng)該不是一人一時之作,而是經(jīng)過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而這也符合早期著作的形成規(guī)律。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又有毛公之學(xué),自謂子夏所傳。”所謂“自謂”,就是自說自話的意思,可見班固也不大相信“毛詩”的解說是子夏所傳。不過今天學(xué)者考證“毛詩”確實有不少戰(zhàn)國時期儒家思想淵源,《詩大序》也與《禮記·樂記》相關(guān)材料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但淵源是一回事,“作”又是另一回事。
當然,從目前材料來看,《毛詩序》的完整性、系統(tǒng)性是其他三家不能比擬的。傳世材料中從未見過“三家詩”有類似《詩大序》,目前只有各詩前面的小序,而且海昏侯《詩經(jīng)》簡中并不是每一首詩都有這樣的序。這就涉及“毛詩”與“三家詩”解釋方式的問題,這一點有待海昏侯《詩經(jīng)》簡全部公布后,會帶來新的認識和討論。清代學(xué)者皮錫瑞曾指出“論《詩》比他經(jīng)尤難明”,并舉出8個方面,最后一條就是“三家序亡,獨存毛序,……究竟源出西河(子夏),抑或出于東海(衛(wèi)宏),此詩之難明者八也”(《經(jīng)學(xué)通論》卷二)。相信海昏侯《詩經(jīng)》簡會為我們揭開學(xué)術(shù)史上的一個又一個迷霧。
《詩經(jīng)》自結(jié)集之后,相對而言是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文本,不像《尚書》有真?zhèn)螁栴}的討論,故一直以來被視為兩周時期最可靠的文獻材料,也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詩歌選集。由于它是周代禮樂文明的產(chǎn)物,有關(guān)它的功能、性質(zhì)、特征,都帶有很深的禮樂文化烙印。孔子以它來教育弟子,戰(zhàn)國時期學(xué)者不斷傳承、運用與闡釋,在《詩經(jīng)》的解釋上疊加了儒家政治倫理道德思想,這些淵源與思想被漢代學(xué)者吸收,成為系統(tǒng)學(xué)說,影響深遠,構(gòu)成了歷史上理解《詩經(jīng)》的重要基礎(chǔ)。然而漢代詩說畢竟流傳不多,只留下些許碎片,難以拼湊出漢代《詩經(jīng)》學(xué)的全貌。海昏侯《詩經(jīng)》簡的出土,無疑是一塊重要的“拼圖”,既豐富了《詩經(jīng)》學(xué)淵源,又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詩經(jīng)》解釋傳統(tǒng)的形成,進而更好理解和發(fā)掘中國古代《詩經(jīng)》學(xué)的特質(zhì)。
(作者:于浩,系南昌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院副教授)
【編輯:董麗娜】
文章、圖片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