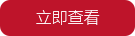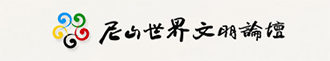桃李情深 歐陽修與蘇軾的師生情誼
2025-09-14 16:33:44 作者:陳彧之
中國素有尊師重教的傳統,留下了許多教學相長、師生情深的佳話。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與蘇軾兩人的師生情,令人動容,他們一生見面的次數并不多,通過詩文進行互動,彼此欣賞、相互寬慰,直至今日,我們還能在一些著名景觀中感受到兩人的師生情深。
慧眼識珠寄予厚望
北宋熙寧四年(1071),歐陽修致仕。蘇軾在祝賀老師歐陽修致仕的一篇文章中,盛贊歐陽修“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并說自己“受知最深,聞道有自”。
“文章百世之師”或有夸張之嫌,但歐陽修在北宋文壇的崇高地位卻是毋庸置疑的。他領導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倡導寫作古文,推崇唐代韓愈的古文,對于韓愈文與道兩者的關系既有繼承也有自己的思考。誠如現代學者王水照、崔銘在《歐陽修傳》中指出,“韓愈論‘道’,主要指儒家的禮治秩序、倫理關系”,“歐陽修卻強調‘切于事實’,突出‘道’的實踐性品格,大大縮短了‘道’和人們的心理距離”。歐陽修強調文道并重,不能同意那種視文為傳道的工具的觀點,對于古文的寫作技巧、審美價值,也須下一番功夫研究。
韓愈的古文有“尚奇”的一面,后來一些人竟將這種風格發展為“險怪奇澀”,北宋初期的太學流行此風,所以稱為“太學體”。歐陽修反對“太學體”,利用自己執掌嘉祐二年(1057)貢舉的機會,他決定掃除積弊、刷新文風,凡以“太學體”為文的考生皆遭黜落。
如此雷霆手段,使久習“太學體”的考生一時難以接受,考試結束后,有考生在路上圍堵歐陽修,“聚噪于馬首”,街上巡邏的人無法制止。他們表達自己的不滿,但并未改變歐陽修革新文壇風氣的決心,眾人亦不得不承認“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嘉祐二年貢舉,共有388人登榜,其中有來自陜西的張載,有來自江西的曾鞏和他的五位至親,有來自四川的蘇軾、蘇轍兄弟,可謂群星燦爛,這一榜被稱為“千年科舉龍虎榜”。這一年,歐陽修51歲,蘇軾21歲。
宋人好寫筆記,將蘇軾初出茅廬的不凡氣度寫得傳神無比。閱卷過程中,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深得歐陽修、梅圣俞等考官的欣賞,歐陽修想列為第一名。考官閱卷時,并不知道文章出自哪位考生之手,歐陽修推測也許這篇雄文是自己的學生曾鞏寫的,為了避嫌,遂將其列為第二名。待到放榜之時,方知其作者并非曾鞏,而是蘇軾。
蘇軾的這篇文章中,提到了一個典故,說堯帝時,有個人犯了罪,法官皋陶三次要殺之,堯帝三次寬宥之。博學如歐陽修者,不知此典故出自何處。放榜之后,蘇軾前來拜謝歐陽修,歐陽修竟還想著這件事,問那個典故出自何處。蘇軾說出自《三國志·孔融傳》。蘇軾離開后,歐陽修翻閱《三國志》,卻并未在《孔融傳》中發現這一典故。待到下一次相見時,歐陽修再度提起,蘇軾表示孔融曾有“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之語,他依據堯帝的仁厚與皋陶的嚴格推測應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歐陽修聞之大喜,稱贊蘇軾“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歐陽修與蘇軾通過科舉結成了師生關系,這種關系的維系有賴于雙方的信任與互動,歐陽修選擇了蘇軾,蘇軾也選擇了歐陽修。歐陽修身為當時文壇的執牛耳者,對蘇軾的文學理念、文學才華給予充分肯定,他在蘇軾身上看到了自己革新文風的事業后繼有人,他高興地表示“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此語令人想到韓愈《師說》中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蘇軾日后不負老師所望,在一波三折的人生歷程中,錘煉出一篇篇飽含真情、富有哲理的傳世佳作。
泛舟西湖諄諄教誨
說到西湖,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杭州西湖。世間不只杭州有西湖,對于歐陽修而言,他沒有游覽過杭州西湖,卻對潁州西湖情有獨鐘。
慶歷五年(1045),范仲淹、韓琦等主持新政的大臣遭貶,一向勇于直言的歐陽修為他們辯護,他以篤定的口吻說“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他為范仲淹、韓琦等人遭貶感到惋惜。歐陽修此番言論招致政敵的痛恨,不久他也遭貶。他先是到滁州、揚州為官,皇祐元年(1049)獲準移知潁州(今安徽阜陽)。
歐陽修喜歡潁州這個不大的地方。潁州城外有一片浩渺的水面,便是潁州西湖。歐陽修曾引西湖水灌溉農田,又創立了西湖書院,大興文教。他初至潁州西湖,便覺相見恨晚:“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歐陽修固然來遲了,但總算是來了,來了就不想離開。
他萌發了終老于此的愿望。十八年后,即治平四年(1067),歐陽修去往亳州任職的途中,獲準在潁州小住一月。他將自己離開潁州后思念潁州的詩作予以整理,所撰《思潁詩后序》說:“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于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
這個愿望終于在其于熙寧四年致仕后得以實現。歐陽修寫下十首《采桑子》,歌詠不同時節下的西湖風光。他如此寫潁州西湖的春景:“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這首小令語言生動、清新,詞人也必然是在愉悅的心境下寫成。
令歐陽修更為高興的是,熙寧四年,學生蘇軾和其弟蘇轍來潁州看望自己。師生二人已有幾年不見,共游西湖,飲酒賦詩,何其樂也。蘇軾有《陪歐陽公燕西湖》一詩,“謂公方壯須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這一年,歐陽修65歲,蘇軾35歲,見到老師的氣色不錯,蘇軾很開心,開心地為老師跳起舞來,祝他長壽、健康,“插花起舞為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
在“醉后劇談猶激烈”的瀟灑之外,歐陽修亦語重心長地告訴蘇軾:“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歐陽修所傳授的不僅是為文的道理,亦是為官、為人的道理。
元祐六年(1091),蘇軾來到潁州為官,回憶起共游西湖的美好時光,想起老師的諄諄教誨,蘇軾“垂淚失聲”。在一篇祭歐陽修與夫人的文章中,他寫道:“白發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蘇軾的懷師之情真摯無比,這化作了他治理潁州的動力,他沒有辜負老師的恩情,也沒有辜負潁州人的注目。
泉名六一師恩難忘
熙寧四年,蘇軾是在去往杭州的路上,到潁州拜訪歐陽修。由于對變法措施多有不能認同之處,蘇軾外放杭州,擔任了三年杭州通判。在潁州與歐陽修相聚時,歐陽修豈會不知學生心中的失望與落寞,他向蘇軾介紹了自己在杭州西湖孤山的一位朋友惠勤,此人“甚文,而長于詩”,歐陽修曾寫三首《山中樂》相贈。他對蘇軾說:“子間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間而不可得,則盍往從勤乎?”在公事之余,蘇軾若想尋一位能同游湖山的雅士,排解自己的情緒,不妨就去找這位惠勤。蘇軾到任第三天,就去孤山找到了惠勤,因為有共同的師友歐陽修,他們很快就成為了知己。
熙寧五年(1072),歐陽修終老于潁州。噩耗傳來,蘇軾與惠勤俱悲傷不已。蘇軾的哀傷,在其《祭歐陽文忠公文》中可見一斑,他贊揚老師的人品與風骨,感恩老師對父親蘇洵的推薦、對自己的提點與教誨,“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于門下者,十有六年于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十六年前,即嘉祐二年,蘇軾以一篇揮灑自如的文章,得到了歐陽修的青睞。一切似乎都只在眼前,轉頭卻已不見恩師影、不聞故人聲。
蘇軾兩度來杭州任職,留下了整治西湖、修筑蘇堤、營造景觀的佳話。在孤山南麓一角,一個很容易為人忽視的景觀,是蘇軾對老師歐陽修深深的思念。
元祐四年(1089),蘇軾出任杭州知州。他向西湖孤山走去,試圖尋找惠勤,方知舊友也已離開人世多年。在惠勤的舊居中,他的弟子接待了他,望著墻上懸掛的歐陽修與惠勤的畫像,蘇軾心中感慨萬千。
說來也怪,在蘇軾造訪惠勤舊居幾個月之后,一口泉水忽涌出于宅后,“汪然溢流,甚白而甘”。他將這口泉命名為“六一泉”。歐陽修退居潁州后,自號“六一居士”。在《六一居士傳》中,歐陽修向客人解釋此名之由來,“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如此算起來只有五個一,歐陽修繼續解釋,“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
歐陽修從未到過杭州西湖,蘇軾卻將西湖邊一口泉命名為“六一泉”,他也須向眾人解釋何以如此命名。在《六一泉銘并敘》中,他說:“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后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于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于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余烈,亦或見于斯泉也。”泉澤蒼生,如歐陽修這樣的君子,其福澤能傳百世。歐陽修的人格風范使學生蘇軾受益無窮,蘇軾堅信還將有更多人受到老師的影響。
蘇軾想象自己與老師共登孤山、共飲泉水的場景,夢是虛幻的,泉卻是真實的。憑借這樣一種機緣,歐陽修竟與杭州西湖有了聯系。今天,我們仍可來到六一泉前,不妨想象歐陽修與蘇軾這對師生坐在泉邊,談詩論藝,擊節贊嘆,一如那年共游潁州西湖時暢快。
【編輯:】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