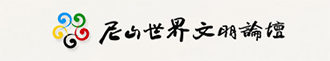朱熹“驚心動魄”的監察謀劃
2025-09-13 14:17:19 作者:李偉
淳熙八年(1181年)三月的浙東地區,伴隨著接續不斷的大雨,成了一片汪洋澤國。
基于南康軍賑災的成效,三月二十五日,51歲的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受命主持賑災事宜。
關于嚴重的災情,朱熹曾在給呂祖謙的信中憂嘆:“聞浙中水潦疾疫,死者甚眾,聞之使人酸鼻。”而今,適逢其會,兼濟天下蒼生,正好可一展身手。
一
事無準備不立。經歷過南康軍賑災時個別官吏的橫征暴斂、中飽私囊等棘手問題的朱熹深知,在這么大的范圍賑災,最好能得到宋孝宗趙昚的首肯或支持。于是,朱熹上書請求赴任前入都奏事。但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他才得到孝宗的召見。
救災如救火。延和殿上,因入都前經衢、婺、紹興時已詳細探尋各地災情,朱熹對此已了然于胸,于是面奏七札,對賑災措施進行了全面陳述。盡管孝宗置詞不多,實際上也未給予多有力的支持,但終究“上為動容”,朱熹還是得到了一些“恩準”,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一些事情了。
按照慣例,賑災多采取“權免稅役”“蠲減租賦”等措施,即免去先前積欠的租稅等。這一次,可能鑒于災情的嚴重,又“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賑濟。這一數額其實不算多,大約可以買2500萬斤米,按照當時七州的人口算,大約人均11斤米,可見只是權且救急。
對此,朱熹的謀劃是勸諭上戶獻米(可以蒙恩補授官職),再加上朝廷撥款,大體能渡過劫難。但思慮細密的他沒有意料到,一場大的災難正突襲而來。
朱熹擔任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巡歷覺察,禁止私販,按劾不法”。第二年七月十六日,風塵仆仆趕路的他道遇臺州流民47人“扶老攜幼,狼狽道途”,問之原因,皆云“旱傷至重,官司催稅緊急”所致。又因問知臺州的唐仲友“多有不公不法事”。情急之下,朱熹上了按劾的第一狀。二十三日,一到臺州,又馬不停蹄地寫了第二狀,具體解釋唐仲友如何催逼:此人將朝廷規定交納夏稅的期限提前了2個月,派人四處催逼;甚且天臺縣僅納了一半左右,其知縣趙公植就被捉押到臺州,強令交納換取。進一步“密切體訪”,審問、核實后,又上了第三狀,進行詳細的陳述,共24條。這是朱熹彈劾的重點,概括來說,就是唐仲友多方盤剝,一郡皆以為苦;“以饋送為名”,盤織了一張地方、朝廷的關系網等。
但這三道彈劾,都被宰相王淮扣押,藏匿不報。等了十多天后毫無動靜,八月八日,朱熹又上了第四狀。這相當于對第三狀的補充,通過審問相關人犯一一確認情節。但面對審查,唐仲友竟將關鍵的證據“公庫簿歷(賬本)收藏,追索不出”,公然抗拒,最后只得根據“唐仲友拘守不盡草簿”來核查。朱熹不肯放棄,又上了第五狀,直指唐仲友“狂悖無忌憚之氣”是因背后龐大的關系網,具體來說,就是宰相王淮之妹是唐仲友弟弟的妻子,在背后為其撐腰。這一明言,其實是朱熹的破釜沉舟。所以,八月十四日,朱熹再上了一道《乞罷黜狀》,直接陳明唐仲友不過是想“拖延旬月,等候赦恩”,來逃避懲罰。但九月四日,朱熹竟知自己已被剝奪浙東提舉半個月了。他如夢方醒,這就是個騙局。于是,他搶在詔命正式下達到處州時,憤而上了第六狀,表明自己絕不低頭的決心。
二
對唐仲友的罪行,朱熹通過親見、路遇察問、拘人審訊、鎖定關鍵證據(賬本)、不厭其煩地多方調查、探訪等,也即其所強調的不辭辛苦,“密切體訪”。
那朱熹所彈劾的罪行,到底重不重呢?
主要看兩大方面:其一,多方盤剝十二萬貫。臺州時轄四縣(寧海、天臺、仙居、黃巖),與今大體一致,臺州的經濟情況實為一般,《嘉定赤城志》卷七就徑直言掙錢的頂梁柱“茶場既廢二鹽監改隸他郡(歸他州管轄)”,僅有措置得宜,方可“使州用無匱而民力不傷”,但一般很難做到。前不久,淳熙二年(1175年),知臺州的趙汝愚就感慨“凜凜然若履薄冰之上,而進退維谷也”。趙汝愚一心為臺州,在任上曾極力重修事關臺州安危的城門。1173年,知臺州的尤袤也寫過《臺州》詩,傾訴其官臺州的不易:“百病瘡痍費撫摩,官供仍愧拙催科。自憐鞅掌成何事,贏得霜毛一倍多。”兩年間,因悉心操勞,尤袤兩鬢白發竟添了一倍多;還因不愿多催逼百姓,拖欠國庫錢財長達8年,因此被“特降一官”。這種情形下,唐仲友能理財、貪污到如此之多的數額,確實是“不容易”了。同樣據《嘉定赤城志》載,上供的折帛錢不過二十二萬六千余貫,經總制錢十五萬六千余貫。這樣看來,唐仲友一年盤剝的幾近上供的經總制錢,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量。
其二,縱容、威逼蔣輝造假幣,更是殺頭的重罪。據南宋的會子法令,“敕偽造會子犯人處斬。賞錢壹阡貫”(國家博物館就藏有一貫面額的會子銅印版)。
這都是重刑。但是,在朝中右相王淮的斡旋下,陳述唐仲友累累罪行的第二、三、四狀被壓下,只有寥寥數語的第一狀同唐仲友詳細的自辯呈報給孝宗,整件事被輕描淡寫,這只是“秀才爭閑氣”,類似吃飽了撐的。
某種程度上,這正中孝宗下懷——因朱熹前前后后上了那么多的奏折,甚且在延和廷對時,還專意斥責孝宗拒諫聽讒、文過飾非等惡習,甚至上升到君主一心不正的高度——顯然是以理學家的準則來苛求皇帝,已經惹得孝宗內心有絲絲不滿。這回正好能擺脫,落得個耳根清凈。于是,為了堵住天下眾人之口,唐仲友被免職(其他從犯沒被發落)。
憤怒之下,朱熹只有用辭官歸隱來表達最后的抗爭,掙得一些顏面。在這張用宗法血緣的姻黨與官僚特權編織的封建巨網面前,朱熹在《辭免江東提刑奏三》中已有清醒的認識:“臣所劾贓吏,黨羽眾多,棋布星羅,并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馳騖經營于下……其加害于臣,不遺余力”——他注定以失敗告終,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不過,朱熹贏得了公譽,一代名士陸九淵在給陳倅的信中就贊揚“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政一事,尤快眾人之心”;耿直的陳亮也說:“物論皆以為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
是非曲直,自有公道。這款款陳曲,正見出民心所向。
只是,當朱熹決計再次回到秀美的武夷山九曲溪的武夷精舍隱居,從此“杜門讀書,自余真可付一大笑”時,他不知道的是,吏部尚書鄭丙已上了一道奏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監察御史陳賈也曲意附和——一場更大的風雨,針對道學、席卷全國的“慶元黨禁”已悄然拉開了序幕……
時日雖逝,仍不由得讓人掩卷而思。
【編輯:】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