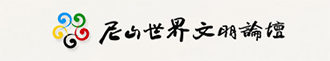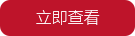海岱間,“山東人”李白有著何等際遇
2025-11-12 16:57:52 來源:大眾新聞 作者:盧昱
1280年前,唐天寶四年(745年)深秋,魯郡東石門(今兗州境內(nèi))外,泗水河畔,一座古老的石壩橫臥水面。這便是金口壩,一處引汶入泗、灌溉千頃良田的水利樞紐,也是兗州通往曲阜的必經(jīng)之路。此刻,壩上寒風(fēng)蕭瑟,落葉紛飛,45歲的李白與34歲的杜甫正依依惜別。
李白接過杜甫遞來的杯中酒,一飲而盡,臉上不見往日的疏狂,只有一種深沉的落寞。他寫詩道:“醉別復(fù)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yuǎn),且盡手中杯!”
飛蓬無根,隨風(fēng)飄蕩,這是他們共同的命運寫照。這場金口壩話別,是李白在山東斷斷續(xù)續(xù)20余年的驚鴻一瞥。山東,不是李白人生的起終點,卻是他生命拼圖中最完整、最耐人尋味的一塊。他對山東之熟悉、熱愛及贊頌,甚至讓人誤以為他是山東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里說:“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舊唐書·李白傳》也稱李白是山東人。讓我們溯流而上,探尋“山東人”李太白在海岱間,有著何等際遇。

徂徠山下:佯狂者的避難所
讓我們將目光投向金口壩話別10年前的徂徠山。
那時,李白被功業(yè)未成的焦灼、與生俱來的豪俠之氣裹挾,他必須尋找一個宣泄的出口。于是,他常常從兗州北上,進入徂徠山深處。那里有一條清淺的溪流——竹溪。溪畔林木幽深,遠(yuǎn)離塵囂。
在這里,李白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失意文士:孔巢父、韓準(zhǔn)、裴政、張叔明、陶沔。這六人,因共同的失落與不甘聚在一起。他們?nèi)杖蘸ǜ杩v酒,笑傲山林,被時人稱為“竹溪六逸”。

(徂徠山)
月光如水,傾瀉在竹林之上,溪水潺潺,如同低語。六人圍坐一塊平坦的大石上,酒壇散落。孔巢父擊節(jié)高歌,韓準(zhǔn)醉臥石上,李白則拔劍擊石,發(fā)出清越之聲,隨即朗聲吟誦:“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歌聲與笑聲,在寂靜的山谷中回蕩。
這并非一場附庸風(fēng)雅的聚會,而是一場精神的保衛(wèi)戰(zhàn)。這些人要求突破各種傳統(tǒng)約束羈絆:他們渴望建功立業(yè),獵取功名富貴,進入社會上層;他們抱負(fù)滿懷,縱情歡樂,傲岸不馴,恣意反抗。而所有這些,又恰恰只有當(dāng)他們這個階級在走上坡路,整個社會處于欣欣向榮并無束縛的歷史時期中才可能存在。而竹溪,成了他們的精神堡壘。
狂歡的背后,有著深不見底的悲涼。李白在《送韓準(zhǔn)、裴政、孔巢父還山》中寫道:“獵客張兔罝,不能掛龍虎。所以青云人,高歌在巖戶。”這幾句詩,道盡了他們內(nèi)心的矛盾。
“獵客”本應(yīng)去捕獵龍虎這樣的猛獸,卻只能張網(wǎng)捕兔;胸懷青云之志的人,卻在山野巖洞中高歌。他們的“逸”,不是超脫,而是清醒者痛苦的佯狂。竹溪的酒再烈,也澆不滅心中那團“功業(yè)”之火。他們在醉鄉(xiāng)中逃避現(xiàn)實,又在清醒時痛感逃避的徒勞。徂徠山的竹林,既是他們的樂園,也是他們的牢籠。
七年后,李白奉召入長安時,曾寫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豪言。這句詩的底氣,或許源于徂徠山的經(jīng)歷。正是在那里,他確認(rèn)了自己的與眾不同,也積蓄了在政治旋渦中沉潛的勇氣。竹溪六逸,是李白走向長安前的演練場。
雙行桃樹下,撫背復(fù)誰憐
當(dāng)我們從徂徠山的竹林深處走出,轉(zhuǎn)向兗州城內(nèi),會發(fā)現(xiàn)一個截然不同的李白。
李白住在兗州哪兒?正如他詩中所說:“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沙丘無漂母,誰肯飯王孫?”“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沙丘,便是李白家之所在。“其實,沙丘就是瑕丘。近年來在泗河出土的殘石上,更兩次出現(xiàn)沙丘字樣。一是北齊時候的一件石碑,有‘以大齊河清三年歲次實沉于沙丘東城之內(nèi)’的話語;另一件殘破過甚,但尚存‘唐開元十六年……俗姓常氏山陽沙丘’字樣,這說明,至少從北朝到唐代,瑕丘就有沙丘這樣一個別稱。”兗州文史專家樊英民先生認(rèn)為。

(1903年的兗州)
若進一步追問,李白的家在瑕丘什么位置?從李白作品中也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今晨魯東門,帳飲與君別”“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jīng)年”“月出魯城東,明如天上雪”。這里的魯東門、魯門東、魯城東者,應(yīng)就是他家的所在地。魯東門者,唐魯郡治所瑕丘城之東門也;魯門東、魯城東者,瑕丘城東門之外也。具體到今天,大約在兗州火車站一帶。那里過去多沼澤低洼之地,所以李白有《魯東門觀刈蒲》之作;那里距泗河、豐兗渠不遠(yuǎn),所以李白可以月下泛舟;那里距堯祠石門也不遠(yuǎn),所以李白送竇薄華于堯祠,雖是久病初起,也能“強扶愁疾向何處?角巾微服堯祠南”。
李白到兗州定居時,安陸的許氏夫人約已故去,一雙兒女隨他同來。姐姐平陽大約五六歲,弟弟伯禽只有兩三歲。到瑕丘后,李白又結(jié)了婚,婚姻生活并不美滿:“先合于劉,劉訣;次合于魯一婦人。”這個魯婦人不知因何,離家而去。李白在這里薄有田產(chǎn),家中還有酒樓,樓下栽有桃樹。
李白雖以天下為家,卻始終心系一隅——山東。寓居山東二十年光陰,他過著有家、有友、有詩、有酒的人生。他的許多代表詩篇,或醞釀于徂徠山下的松風(fēng),或揮毫于泗河舟中的月夜。此地非僅棲身之所,實為其詩思沉淀、情感扎根的土壤。李白一生作詩數(shù)千首,可因時代動蕩,“十喪其九”;今存可靠詩作900余首,雖非全貌,卻是盛唐詩歌的頂峰。現(xiàn)存詩歌中,大約有60首與山東有關(guān)。
可惜,李白夙有“濟蒼生安社稷”的宏大抱負(fù),事實卻“欲渡黃河冰塞川”。他在慨嘆“行路難”的同時,只有沉淪于詩酒和浪游在天涯,這也使得他在時間上陪伴子女不多。
李白對孩子的教育,有著陶淵明“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的達觀。他寫給子女幾首詩可謂舐犢情深,如:“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jīng)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yīng)駕小車騎白羊。”“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fù)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
我輩豈是蓬蒿人
李白42歲時,人生迎來巨大轉(zhuǎn)折。由玉真公主的舉薦,玄宗皇帝征詔他入京。公元742年夏,李白有泰山之行。秋初,他回兗州不久,便接到朝廷詔書。李白自然狂喜不禁,這充分反映在《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中。
“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yuǎn)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詩中的會稽愚婦,明顯指那位棄他而去的“魯一婦人”。而南陵,據(jù)文史學(xué)家王伯奇先生考證,即今兗州東關(guān)九仙橋北的南沙崗。南沙崗以南不遠(yuǎn)是豐兗渠(今府河),渠南是驛道,渠上有九仙橋。李白的兒女送他西去長安,正好經(jīng)過南沙崗。
李白進京后,玄宗皇帝授以翰林供奉。御調(diào)羹,金床相迎,也著實風(fēng)光了一段時間。但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自己在皇帝心目中不過是一個高級俳優(yōu),所謂安邦定國經(jīng)世濟民的大志根本沒有可能實現(xiàn)。當(dāng)時的朝政被把持在李林甫、楊國忠之流的手中,正直耿介之士無不遭到壓制和排擠。不久,李白就受到讒害,漸漸被皇帝疏遠(yuǎn)。

(長安城,影視劇《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天寶三載(744年)春,李白上疏乞還,玄宗詔許賜金還山。
長安的經(jīng)歷,對李白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正是這次放還,讓他在孟夏時,在洛陽遇到杜甫。當(dāng)時,杜甫寄居姑父家里。他的姑姑這時已去世,杜甫留下來,目的是想結(jié)交人脈,為未來出仕做官作準(zhǔn)備。
兩個不算得意的人,因詩歌之名,一見如故。兩人到底去了哪些地方,見了哪些人,已無從考證。可以想象的是,在洛陽這個繁華都會,兩人少不了酒肆買醉,登高賦詩,過得很是逍遙。
那時的李白,論風(fēng)采,神仙中人;論做派,豪氣干云;論詩才,驚神泣鬼。他是從天而降的一道光,照亮了杜甫苦悶而平庸的生活。在那個靠馬蹄與腳步丈量世界的年代,兩位偉大詩人于茫茫人海中相逢,實屬奇跡。
夏秋之際,他們又結(jié)識了當(dāng)時已經(jīng)十分有名的詩人高適,三人相攜同游梁宋,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開封和商丘,登臨鼓吹臺和單父琴臺,一路飲酒對詩,暢懷古今。
離別后,李白先回到兗州,冬游河北,再至濟南,在齊州紫陽宮正式受箓?cè)氲溃瑥拇恕吧碓诜绞扛瘛薄K簧钍艿兰宜枷胗绊懀倌陼r代就曾訪道蜀山。好友中元丹丘、吳筠等都是道門中人。因而,李白眼中的神仙境界,不是不可到達的彼岸,而是一種來處與歸宿。
總為從前作詩苦
天寶四載夏至天寶五載,李白、杜甫、高適又在泰山南北、汶河之畔留下身影。
他們來到濟南,與北海太守李邕等文壇巨擘聚集一堂,高歌長吟。杜甫寫了一首《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今日歷下亭)
天有不測風(fēng)云。天寶六載(747年)正月,李邕遭受誣陷,被奸相李林甫投入大牢。李邕以七十歲高齡在北海郡,也就是青州任上橫遭杖殺。
噩耗傳來,杜甫不勝悲憤,寫有《八哀詩·贈秘書監(jiān)江夏李公邕》。李白也抑制不住憤怒大聲疾呼:“君不見,李北海,英風(fēng)豪氣今何在?”
歷下盛會以后,杜甫北上臨邑(今德州臨邑縣)看望擔(dān)任縣令的弟弟杜穎,李白南返兗州家中。
而后,杜甫惦記著李白,便來兗州尋李白。

李白的詩詞中,有一首題為《戲贈杜甫》的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這首詩曾一度被認(rèn)為是偽作,有專家則確信其真,并指出,從李杜的交游來考察,此詩似寫于魯中,即“李白偕杜甫、高適醋獵孟諸分手之后,再次相見之初。飯顆山或為兗州之小地名,故鮮為注家所知”。那么,飯顆山在哪里呢?樊英民以為,也許就是今兗州城北石馬村后的土崗甑山。
兗州的地勢是一馬平川的大平原,除了城西小小的嵫山外,并沒有山。清末周元英編的《滋陽縣鄉(xiāng)土志》卷三“山水”記有:“甑山,在城北五里余石馬村后。無石,地勢所聚,高若大阜,方圓六七里,有柏樹數(shù)十株,樹木蔭沉,森然毓秀。”
另外,《滋陽縣志》所記的兗州八景中有一景是“龍山環(huán)照”,所謂龍山其實是城南泗河以北的一段蜿蜒曲折的土崗。兗州人習(xí)慣把高大的土崗稱為山,恰如習(xí)慣于把低洼的地區(qū)叫“湖”或“海”。至今魯南地區(qū),還有民俗稱呼“下地”為“下湖”。
石馬村北的土堆稱“甑山”,是因其形似甑。清人牛運震作《春日兗州覽古賦》,其中歷數(shù)兗州名勝古跡,有“甑山象其形”之語。“甑”與“飯顆”的聯(lián)系是不言而喻的。甑山恰位于瑕丘城北的官道一側(cè),若李白和杜甫一同去城北訪問范居士,甑山便是可歇足的必經(jīng)之地。
李白在詩中寫杜甫絕無輕薄嘲諷,而是一種帶著關(guān)切的親昵調(diào)侃。杜甫此時年逾三十,尚未顯達,生活清苦,且作詩嚴(yán)謹(jǐn)刻苦,身形清癯。李白以老友口吻笑問其瘦,既顯親密,又暗含對其“苦吟”風(fēng)格的溫和打趣。兩人在正午陽光下相視而笑,一個問:“你怎么瘦成這樣?”一個答:“還不是為了寫詩!”
兩人相逢后,與好友登高望遠(yuǎn),飲酒賦詩。由于泰山就在兗州境內(nèi),他們一定聊到了泰山。杜甫由此向北望向泰山,泰山那邊云起雨驟,他不禁感慨萬千,寫下詩句:東岳云峰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此后,杜甫與李白又一起游覽了東蒙山,尋訪道教名士董煉師及元丹丘,訪問了魯郡城北的隱士范十。
對此,杜甫寫下一首《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fā),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云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與討莼羹。不愿論簪笏,悠悠滄海情。詩中“醉眠”一聯(lián),寫盡了兩人親如弟兄的情景。
李白也有記訪范十的詩,題為《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詩中描寫在一個雁聲陣陣的秋日,他乘興之所至,騎馬到瑕丘城北訪問被稱為“范野人”的老朋友,不小心迷路了,跌落雜草叢生的城壕,弄得他華美的衣服上沾滿了多刺的蒼耳子,即“不惜翠云裘,遂為蒼耳欺”。待他到了范野人家,老朋友看著他狼狽不堪的樣子,不禁哈哈大笑,一面為他仔細(xì)地摘掉身上的蒼耳,一面安排酒菜,用園中自種的蔬菜瓜果招待他。他們開懷暢飲,無拘無束地互相開著玩笑,一直喝到酩酊大醉。“酣來上馬去,卻筆高陽池”,覺得這場痛飲比起有名的晉代名士山簡的高陽池大醉也毫不遜色。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
酒永遠(yuǎn)喝不完,時間卻耽擱不起。李杜各自有事在身:杜甫要西入長安,李白則想重游江東。兩年時間的交游,二人情同手足,離別之際,依依難舍。酒自然喝得不少,李白作有《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幾天之后,還舍不得分別,要繼續(xù)喝。第二次宴別。兄弟兩人舉杯相勸,連連灌酒,又是喝得醉眼蒙眬。李白寫下了《戲贈杜甫》和《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杯中酒一飲而盡,終是要離別了,互道了珍重,兩人眼含淚水,踉踉蹌蹌地分手了。
只是,造化弄人,此次一別,兩位大詩人再未相見。
此后,李白在兗州家中寫下《夢游天姥吟留別》,作為他準(zhǔn)備離開瑕丘南游吳越時的宣言書。此詩以恢宏的氣勢、瑰奇的想象,充分顯示了李白浪漫主義詩人的氣質(zhì),抒寫了他對光明美好的向往和對黑暗丑惡的蔑棄,詩的最后吶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道出了他郁積心中的深刻憤懣。
時空漸遠(yuǎn),思念無窮。數(shù)年后,李白在沙丘城想到好友杜甫,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后,本該一劍封喉的酒線,卻索然無味。《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詩留下了他的內(nèi)心情感: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fù)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杜甫更是個重情重義之人,他在乎始終景仰的李白的感情,時時掛牽不已。乾元二年(759年)秋,杜甫寓居秦州,度過了一段相對安穩(wěn)的生活。而李白卻剛剛經(jīng)歷了人生中的至暗時刻。兩年前,他因曾參與永王李璘的幕府受到牽連,流放夜郎。這一年二月,遇赦放還。
杜甫這時在秦州,地方僻遠(yuǎn),只聞李白流放,不知已被赦還。杜甫擔(dān)憂李白安危,數(shù)次夢到李白。夢醒后寫了兩首《夢李白》。其中第二首云:“浮云終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fēng)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fù)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wǎng)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
因為思念之情太深,杜甫會連續(xù)好幾夜都夢到李白。在夢里,兩人相見后互訴衷腸,難舍難分。到了分別的時候,李白總會滿面愁容地感慨,到你這里來一趟真的很不容易。江湖上波譎云詭,小舟隨時會沉沒。說完后,李白便走出門去。杜甫無法挽留,只能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初秋金口壩)
金口壩的訣別,讓我們看到李杜的友誼,更看到立體而矛盾的李白。他不是那個懸浮在歷史天空中的“詩仙”,而是在山東大地上真實行走、呼吸、掙扎與歡笑的詩人。
【編輯:張曉芮】
文章、圖片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 儒學(xué)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暨文化潤疆工作座談會舉辦
- 鄒城:千年古城激蕩高質(zhì)量發(fā)展澎湃動能
- 濟寧:文化“兩創(chuàng)”,讓千年儒風(fēng)“活”起來
- 六百年屯堡 續(xù)古韻新章
- 讓互聯(lián)網(wǎng)更好造福人民、造福世界——2025年世界互聯(lián)網(wǎng)大會烏鎮(zhèn)峰會綜述
- 數(shù)字文博何以向新而活
- 海岱間,“山東人”李白有著何等際遇
- 陸雯:以禮為“橋” 涵養(yǎng)學(xué)子文化自信與時代擔(dān)當(dāng)
- 高揚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世界意義
- 儒學(xué)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暨文化潤疆工作座談會舉辦
- 為中醫(yī)藥文化注入“時代流量”
- 鄒城:千年古城激蕩高質(zhì)量發(fā)展澎湃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