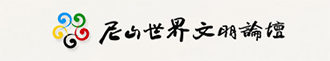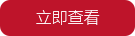翟奎鳳:張岱年論中華民族基本精神及其時(shí)代意義
2025-10-08 12:15:05 作者:翟奎鳳
摘要:在晚清近代,面臨空前生存危機(jī)的中華民族煥發(fā)出強(qiáng)大斗志,自強(qiáng)不息、剛健奮進(jìn)的精神格外突顯。受時(shí)代影響,張岱年早年關(guān)于中華文化的討論也是特別強(qiáng)調(diào)“自強(qiáng)不息”、剛毅進(jìn)取精神的重要性,罕言“厚德載物”的包容、和平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張岱年提出以“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為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到了1990年代,張先生特別突顯“厚德載物”精神的重要性,他認(rèn)為世界各偉大民族皆有“自強(qiáng)不息”的精神,但“厚德載物”的包容、和平精神是中華民族所獨(dú)有的。“自強(qiáng)不息”彰顯了民族主體性、獨(dú)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張先生將“自強(qiáng)不息”的民族精神與愛(ài)國(guó)主義緊密聯(lián)系起來(lái)。民族精神與時(shí)代精神是辯證統(tǒng)一的,立足于新時(shí)代的民族精神,如果繼續(xù)借用《周易·大象傳》話(huà)語(yǔ),可以吸收《周易》下經(jīng)咸恒兩卦的大象辭,將其表述為“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以虛受人”“立不易方”。
關(guān)鍵詞:自強(qiáng)不息 厚德載物 愛(ài)國(guó)主義 主體性 和平性
關(guān)于民族精神的討論,大概始于1900年,在1930-1939年期間特別是1934年前后相關(guān)討論非常密集,不少人把弘揚(yáng)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與發(fā)揚(yáng)民族精神結(jié)合起來(lái)。1980年代以來(lái),關(guān)于民族精神的討論又活躍起來(lái),如劉綱紀(jì)認(rèn)為中華民族精神包括“理性”“自由”“求實(shí)”“應(yīng)變”四大精神(1),謝幼田從“直覺(jué)是中國(guó)思維的出發(fā)點(diǎn)”“和諧與整體性”“中庸的方法與原則”三個(gè)方面論及中華民族之精神(2),等等。
在這些討論中,張岱年先生的觀點(diǎn)影響最大,張先生認(rèn)為《周易》乾坤兩卦《大象》辭“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最能代表中華民族之基本精神。對(duì)于張先生的民族精神觀,遲成勇等人曾做過(guò)解讀與闡釋?zhuān)?)。本文與遲成勇以及相關(guān)研究的角度不同,側(cè)重考察張先生這一論斷的提出過(guò)程,分析其觀點(diǎn)的前后變化,并在此基礎(chǔ)上就民族精神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思考。
一、“自強(qiáng)不息”與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
乾坤為《周易》之門(mén)戶(hù),64卦可謂皆由乾坤兩卦交合變易而來(lái)。《乾·大象傳》說(shuō)“天行健,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坤·大象傳》說(shuō)“地勢(shì)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乾坤兩卦雖很重要,但在古代,“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似并未引起特別關(guān)注。這兩句話(huà)特別是“自強(qiáng)不息”的“崛起”是在近現(xiàn)代。晚清以來(lái),中華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機(jī),一批批有志之士前赴后繼,試圖通過(guò)變法圖強(qiáng)來(lái)振興中華。“自強(qiáng)不息”成為這一時(shí)期振奮國(guó)民精神的響亮口號(hào),在晚清民國(guó)很多報(bào)刊的醒目位置,經(jīng)常有此四字題詞,各界演講和學(xué)人專(zhuān)文也常以“自強(qiáng)不息”為主題主旨,不少高校甚至中小學(xué)也以“自強(qiáng)不息”為校訓(xùn)、學(xué)訓(xùn)。
由于積貧積弱、落后就要挨打的血的教訓(xùn),在近代文化中,我們突出強(qiáng)調(diào)了“自強(qiáng)不息”、奮發(fā)圖強(qiáng)的精神。相對(duì)地,“厚德載物”提得較少。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梁?jiǎn)⒊谇迦A發(fā)表論君子的演講時(shí)認(rèn)為“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最能概括君子修為的基本精神。1920年,《清華周刊》第205頁(yè)有“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題詞,1931年清華《消夏周刊》第7期以“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為校訓(xùn)題詞。
清華校訓(xùn)源自梁?jiǎn)⒊摼拥难葜v,除此之外,“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在近代社會(huì)文化中很少并提。這也可以理解,在近代中國(guó),對(duì)于中華民族而言,首要的是“自強(qiáng)不息”,通過(guò)變革、斗爭(zhēng)來(lái)實(shí)現(xiàn)獨(dú)立自主,擺脫“亡國(guó)滅種”的生存危機(jī)。顯然,“厚德載物”之平和包容精神對(duì)于近代中國(guó)而言是不合時(shí)宜的。
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這種看法影響廣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這是張岱年首先提出來(lái)的,更不清楚張先生是在什么年代提出的。對(duì)張先生這一觀點(diǎn)的具體提出過(guò)程作一考察是必要的。
自1933年大學(xué)畢業(yè)始,張岱年先生曾長(zhǎng)期在清華任教,校訓(xùn)“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對(duì)張先生的為人為學(xué)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但在時(shí)代影響下,張先生早年也是只強(qiáng)調(diào)“自強(qiáng)不息”精神的重要性。張先生在1932年《辯證法與生活》、1933年《世界文化與中國(guó)文化》兩文中只是偶爾提到“自強(qiáng)不息”,并未作特別強(qiáng)調(diào)。1934年,張先生在《中國(guó)思想源流》一文中開(kāi)始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易傳》也是發(fā)揮宏毅哲學(xué)的”,“自強(qiáng)不息”“剛健中正”“表出了中國(guó)固有精神之精髓”(4),認(rèn)為“中國(guó)民族現(xiàn)值生死存亡之機(jī)。應(yīng)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安毅能應(yīng)付危機(jī)的哲學(xué)”“中國(guó)要再度發(fā)揮其宏大、剛毅的創(chuàng)造力量”(《全集》第一卷,第199頁(yè))。
1935年,在《西化與創(chuàng)造》一文中,張先生認(rèn)為“剛健的態(tài)度,主自強(qiáng)不息,生生日新,宰制自然”“我們所要發(fā)揚(yáng)的原有的卓越的文化精神,乃是原始的剛健精神”(《全集》第一卷,第250-251頁(yè)),這里將剛健自強(qiáng)視為我們民族的文化精神之脊梁。在1936年完成的《中國(guó)哲學(xué)大綱》“人生論”部分論及《大象傳》道德修養(yǎng)時(shí),張先生指出“‘自強(qiáng)不息’與‘厚德載物’,實(shí)是《象傳》中的人生思想之中心觀念”(《全集》第二卷,第347頁(yè))。
1944年,在《天人五論》“品德論”中釋“勇”時(shí),張先生指出“勇亦曰剛,亦曰毅,亦曰強(qiáng)”“自強(qiáng)不息,可謂大勇。力強(qiáng)足以勝艱難,志堅(jiān)足以抗險(xiǎn)阻,然后為勇”(《全集》第三卷,第214頁(yè))。總體上看,1949年以前,張先生感于民族時(shí)代,特別強(qiáng)調(diào)宏大、剛毅、自強(qiáng)、勇健之精神,這是一種人格精神,也是一種文化精神。
1980年以后,張先生繼續(xù)強(qiáng)調(diào)“自強(qiáng)不息”的重要性,自強(qiáng)不息不僅是我們的文化精神,也是民族精神。1982年在《論中國(guó)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張先生以“剛健有為”為中華文化四大基本精神之首,指出“天體運(yùn)行,永無(wú)已時(shí),故稱(chēng)為健。健含有主動(dòng)性、能動(dòng)性以及剛強(qiáng)不屈之義。君子法天,故應(yīng)自強(qiáng)不息”(《全集》第五卷,第420頁(yè))。
1984年,在《中國(guó)古代知識(shí)分子與剛健有為、自強(qiáng)不息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中,張先生指出“在《易傳》所宣揚(yáng)的‘剛健’‘自強(qiáng)不息’的思想的熏陶影響之下,中國(guó)歷代優(yōu)秀的知識(shí)分子表現(xiàn)了三個(gè)方面的優(yōu)良品格和作風(fēng):第一,誠(chéng)摯熱烈的愛(ài)國(guó)主義精神;第二,堅(jiān)持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第三,剛強(qiáng)不屈與不良勢(shì)力進(jìn)行斗爭(zhēng)的精神”(《全集》第五卷,第668頁(yè)),這里張先生視愛(ài)國(guó)主義為“自強(qiáng)不息”的首要精神。
1985年2月,在《中國(guó)文化與中國(guó)哲學(xué)》中指出“作為中國(guó)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應(yīng)是剛健有為、自強(qiáng)不息的思想態(tài)度”(《全集》第六卷,第42頁(yè));同年7月,在《孔子在中國(guó)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指出“中華民族有一個(gè)奮發(fā)向上、自強(qiáng)不息的傳統(tǒng),同孔子的影響是分不開(kāi)的”(《全集》第六卷,第86頁(yè))。至此,張先生論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精神傳統(tǒng)時(shí)主要還是強(qiáng)調(diào)自強(qiáng)不息,尚未并提“厚德載物”。
二、“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民族精神的提出
張先生關(guān)于民族精神的討論,一定意義上是在1980年代“文化熱”的大背景下來(lái)展開(kāi)的,與其文化上主張“綜合創(chuàng)新”說(shuō)是同時(shí)期提出的,這些都是在1984年之后的思想。張先生晚年回憶說(shuō)“1983年以來(lái),國(guó)內(nèi)出現(xiàn)了討論文化問(wèn)題的熱潮,這是80年代學(xué)術(shù)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全集》第八卷,第102頁(yè)),“1984年以來(lái),國(guó)內(nèi)文化熱興起,我明確提出‘綜合創(chuàng)新’的觀點(diǎn),并且著重揭舉了‘民族精神’的問(wèn)題,認(rèn)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可稱(chēng)為‘中華精神’,其主要內(nèi)容可以用‘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來(lái)表述。這些見(jiàn)解近幾年來(lái)已受到人們的注意,并且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是我感到欣慰的”(《全集》第八卷,第308頁(yè))。
張先生首次明確自覺(jué)地以“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作為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大概是在1985年8月24日在廬山召開(kāi)的中國(guó)哲學(xué)史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上《談中國(guó)哲學(xué)史研究的發(fā)展趨勢(shì)》演講中,他認(rèn)為“應(yīng)該肯定,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東方五千多年,必然有其優(yōu)秀傳統(tǒng)作為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現(xiàn)在我們要達(dá)到對(duì)于民族精神的自我認(rèn)識(shí)”;強(qiáng)調(diào)“‘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就是中華民族不斷發(fā)展、不斷前進(jìn)的思想基礎(chǔ)”(《全集》第六卷,第90頁(yè))。但是張先生對(duì)此沒(méi)有進(jìn)一步詳談,到了1986年,才對(duì)此作了更多展開(kāi)。
1986年4月24日,張先生以《中國(guó)文化的回顧與前瞻》為主題在北京師范大學(xué)作報(bào)告,他認(rèn)為《易傳》“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對(duì)中國(guó)文化起到促進(jìn)作用,是“中華民族延續(xù)發(fā)展的思想基礎(chǔ)”:
天體、日月、星辰,晝夜運(yùn)行,今天太陽(yáng)從東方出來(lái),明天太陽(yáng)也一定從東方出來(lái),太陽(yáng)不會(huì)懶惰,永恒運(yùn)動(dòng),許多行星也是這樣,人就應(yīng)自強(qiáng)不息,永遠(yuǎn)前進(jìn),勉力向上,決不停止。我認(rèn)為自強(qiáng)不息觀點(diǎn)就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lái)延續(xù)發(fā)展的思想基礎(chǔ),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這是一個(gè)方面。另一方面,“厚德載物”,大地包容萬(wàn)物,兼容并蓄,什么東西在地上都可生長(zhǎng),人應(yīng)胸懷廣大,無(wú)所不容。
這些思想觀點(diǎn),在民族關(guān)系上,表現(xiàn)特別明顯。一方面,中華民族是堅(jiān)強(qiáng)不屈的,不向任何外來(lái)勢(shì)力屈服,堅(jiān)決保衛(wèi)民族獨(dú)立。另一方面,主張國(guó)與國(guó)之間的和平,反對(duì)擴(kuò)張主義,我不向你擴(kuò)張,你也不要向我擴(kuò)張,互相保持和平,“協(xié)和萬(wàn)邦”。堅(jiān)決保衛(wèi)民族獨(dú)立,就是愛(ài)國(guó)主義的傳統(tǒng),這是非常可貴的。(《全集》第六卷,第146-147頁(yè))
“自強(qiáng)不息”就是要像日月星辰那樣周流不息、永遠(yuǎn)前進(jìn),“厚德載物”是像大地那樣包容萬(wàn)物、胸懷廣大。這是論君子人格修養(yǎng),拓展到民族精神上,就是一方面獨(dú)立自主、堅(jiān)強(qiáng)不屈,另一方面睦鄰友好、愛(ài)好和平。這里,張先生也把“自強(qiáng)不息”與愛(ài)國(guó)主義、保衛(wèi)民族獨(dú)立聯(lián)系起來(lái)。
1986年4月28日,張先生在中央黨校作學(xué)術(shù)報(bào)告《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分析》,其中第三節(jié)談《國(guó)民性與民族精神》,他說(shuō)“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延續(xù)發(fā)展,必然有自己的精神支柱,這個(gè)也可以叫做民族精神。每一個(gè)偉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全集》第六卷,第136頁(yè)),而《易傳·大象傳》“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這兩句話(huà),在鑄造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方面是自強(qiáng)不息,永遠(yuǎn)運(yùn)動(dòng),努力向上,決不停止,另一方面也要包容多樣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隨便排斥哪一個(gè)方面”;這兩句話(huà)在個(gè)人生活上也有表現(xiàn),但在民族關(guān)系上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自強(qiáng)不息,就是堅(jiān)持民族獨(dú)立,決不向外力屈服,對(duì)外來(lái)的侵略一定要抵抗,保持民族的主權(quán)和獨(dú)立。自強(qiáng)不息用現(xiàn)在流行的話(huà)說(shuō),就是‘拼搏精神’。同時(shí)還要厚德載物,胸懷廣大,不去侵犯別人,保持國(guó)際和平。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我們應(yīng)該加以肯定”(《全集》第六卷,第137頁(yè))。簡(jiǎn)單來(lái)說(shuō),這種精神就是既不受人欺,也不欺負(fù)別人,是一種獨(dú)立、自強(qiáng)、和平的精神。這與在北師大的講話(huà)基本是一致的。
1986年8月2日,張先生在青島中西文化講習(xí)研討會(huì)上發(fā)表講話(huà)《中國(guó)文化的歷史傳統(tǒng)及其更新》,再次談及“國(guó)民性和民族精神”問(wèn)題,他說(shuō)“一個(gè)延續(xù)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個(gè)在歷史上起主導(dǎo)作用的基本精神,這個(gè)基本精神就是這個(gè)民族延續(xù)發(fā)展的思想基礎(chǔ)和內(nèi)在動(dòng)力。在西方,古希臘文化表現(xiàn)了希臘精神,法國(guó)人民強(qiáng)調(diào)法蘭西精神,德國(guó)人民宣揚(yáng)日耳曼精神,東方的日本也鼓吹大和精神。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基本的主導(dǎo)思想意識(shí)可以稱(chēng)為‘中華精神’,‘中華精神’即是指導(dǎo)中華民族延續(xù)發(fā)展、不斷前進(jìn)的精粹思想”,而“‘中華精神’集中表現(xiàn)于《易傳》中的兩個(gè)命題”:
自強(qiáng)不息就是永遠(yuǎn)努力向上,絕不停止。這句話(huà)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奮斗拼搏的精神,表現(xiàn)一種生命力,不向惡劣環(huán)境屈服。這里有兩方面的意思,在政治生活方面,對(duì)外來(lái)侵略決不屈服,對(duì)惡勢(shì)力決不妥協(xié)、堅(jiān)持抗?fàn)帯⒅钡絼倮T趥€(gè)人生活方面,強(qiáng)調(diào)人格獨(dú)立。孔子說(shuō):“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也講過(guò):“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代儒家強(qiáng)調(diào)培養(yǎng)這種偉大人格。這種精神,應(yīng)該肯定。
《易傳》中還有一句話(huà):“地勢(shì)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是說(shuō),要有淳厚的德性,能夠包容萬(wàn)物,這是中華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有宗教戰(zhàn)爭(zhēng),不同的宗教絕對(duì)不相容。佛教產(chǎn)生于印度,卻不為婆羅門(mén)教所容,結(jié)果佛教在印度被消滅了。在中國(guó),儒學(xué)、佛教、道教彼此是可以相容的,這種現(xiàn)象只有中國(guó)才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地勢(shì)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一個(gè)是奮斗精神,一個(gè)是兼容精神。“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這兩點(diǎn)可以看作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現(xiàn)。(《全集》第六卷,第168頁(yè))
這與同年四月份在中央黨校的講話(huà)在觀點(diǎn)上基本一致,在一些細(xì)節(jié)表述上更為豐富了,同時(shí)也有一些新的思考,比如說(shuō)這里強(qiáng)調(diào)了“厚德載物”的包容精神是“只有中國(guó)才有”。“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是儒者的人格精神,也是我們的文化精神、民族精神。1986年9月24日,張先生在董仲舒思想研討會(huì)上發(fā)表《關(guān)于文化問(wèn)題》的講話(huà),他說(shuō)民族精神“是我提出來(lái)的”,“妨礙民族發(fā)展的那不叫民族精神,能夠促進(jìn)民族發(fā)展的才叫做民族精神”(《全集》第六卷,第190-191頁(yè)),“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集中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自強(qiáng)不息是積極奮斗、不畏強(qiáng)權(quán)的精神,厚德載物是包容寬容、“和而不同”的精神。1986年9月11日,在《〈中華的智慧〉前言》中,張先生指出《易傳》雖作于戰(zhàn)國(guó),但仍是孔子學(xué)說(shuō)的發(fā)展,“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既是人生原則,也是民族精神,體現(xiàn)了儒家的智慧。
從1986年開(kāi)始,張先生在自覺(jué)地思考并凝練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在4月、8月、9月報(bào)告的基礎(chǔ)上,1986年底,張先生就此問(wèn)題發(fā)表專(zhuān)文《文化傳統(tǒng)與民族精神》,他指出“民族精神必須具備兩個(gè)條件:一是有比較廣泛的影響;二是能激勵(lì)人們前進(jìn),有促進(jìn)社會(huì)發(fā)展的作用。一個(gè)民族應(yīng)該對(duì)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較明確的自我認(rèn)識(shí)”(《全集》第六卷,第223頁(yè))。
而《易傳》古來(lái)主流認(rèn)為是孔子作的,有著極高的權(quán)威性和影響力,乾坤兩卦又是《周易》六十四卦的綱領(lǐng)和門(mén)戶(hù),其《大象傳》“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的天地精神又能鼓舞人心、激揚(yáng)奮發(fā),在張先生看來(lái),以其作為民族精神是最合適的。傳統(tǒng)文化與民族精神是一體的,張先生強(qiáng)調(diào)“中華民族必有作為民族文化的指導(dǎo)原則的中華精神。古往今來(lái),這個(gè)精神得到發(fā)揚(yáng),文化就進(jìn)步;這個(gè)精神得不到發(fā)揚(yáng),文化就落后。正確認(rèn)識(shí)這個(gè)民族精神之所在,是非常必要的”(《全集》第六卷,第225頁(yè))。
1988年2月20日,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形成演變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一文中,他再次論及民族精神:“廣義的民族精神指一個(gè)民族所有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思想意識(shí),狹義的民族精神專(zhuān)指能起促進(jìn)文化發(fā)展的積極作用的精粹思想”(《全集》第六卷,第356頁(yè)),而《易大傳》“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就體現(xiàn)了這種精粹思想。張先生又說(shuō):
傳說(shuō)《周易大傳》是孔子撰寫(xiě)的,因而在二千年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之中,《周易大傳》具有崇高的地位與廣泛的影響。據(jù)近年史學(xué)家的考證。《周易大傳》應(yīng)是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儒家學(xué)者的著作。《周易大傳》的這兩句話(huà),表達(dá)了當(dāng)時(shí)的進(jìn)步思想。事實(shí)上,“自強(qiáng)不息”是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華夏人民奮斗精神的反映,“厚德載物”是當(dāng)時(shí)華夏人民寬容精神的反映。這種精神在秦漢以后流傳下來(lái)。
中國(guó)人民對(duì)內(nèi)反抗暴政,對(duì)外反抗侵略,表現(xiàn)了堅(jiān)強(qiáng)的奮斗精神。同時(shí)對(duì)于不同的宗教采取兼容的態(tài)度,向來(lái)沒(méi)有發(fā)動(dòng)對(duì)外侵略,表現(xiàn)了寬容精神。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變的,隨時(shí)代的變遷而有消有長(zhǎng)、有進(jìn)有退。當(dāng)民族精神發(fā)揚(yáng)充盛之時(shí),民族文化就發(fā)展前進(jìn);當(dāng)民族精神衰微不振之時(shí),文化也就處在停滯狀態(tài)之中。這也是一條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全集》第六卷,第356-357頁(yè))
《易傳》傳統(tǒng)上被看作是孔子所作,因而影響很大,張先生接受現(xiàn)代主流學(xué)界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易傳》作于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即便如此,它仍是對(duì)孔子學(xué)說(shuō)的發(fā)展,是儒家思想的體現(xiàn)。張先生這里也強(qiáng)調(diào)了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一體性。
1988年12月在《文化體系及其改造》一文中,張先生也說(shuō)到“每個(gè)國(guó)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法國(guó)有法蘭西精神、美國(guó)有美利堅(jiān)精神、德國(guó)有日耳曼精神,等等,“我們也應(yīng)肯定有一個(gè)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一定要發(fā)現(xiàn)這種精神、認(rèn)識(shí)這種精神、理解這種精神,然后發(fā)揚(yáng)提高這個(gè)精神。我認(rèn)為這個(gè)精神就是《易傳》上所講的兩句話(huà):‘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一方面是發(fā)揮主動(dòng)性,積極向上、奮發(fā)努力、永遠(yuǎn)前進(jìn)、堅(jiān)強(qiáng)不屈;另一方面是厚德載物。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不想向外侵略,修建長(zhǎng)城就是個(gè)例證。長(zhǎng)城是一種防御的設(shè)備,不想向外擴(kuò)張,表現(xiàn)了愛(ài)好和平的態(tài)度”(《全集》第六卷,第451頁(yè))。
總體上看,張先生在1980年代中后期提出以“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仍特別突顯“自強(qiáng)不息”、拼搏奮斗、愛(ài)國(guó)精神的重要性,強(qiáng)調(diào)要捍衛(wèi)國(guó)家主權(quán)、民族獨(dú)立,不屈服任何外來(lái)勢(shì)力;同時(shí),他也提出“厚德載物”之包容、和平精神的重要性,并視之為中華民族的特殊性所在。
三、突出民族精神的主體性、和平性
進(jìn)入90年代,張先生更加重視“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作為民族精神的哲學(xué)意義和時(shí)代意義,在闡釋的重點(diǎn)上也發(fā)生一些變化,他更加突出“厚德載物”之和平性特征是中華民族的特殊精神和寶貴品格,同時(shí),在對(duì)“自強(qiáng)不息”的詮釋上也有些新的富有思想性的提法。
1990年7月30日,張先生在《〈周易〉與傳統(tǒng)文化》一文中繼續(xù)強(qiáng)調(diào)《易傳》“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對(duì)塑造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性,認(rèn)為這兩句話(huà)“集中表述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精神。這兩條是以孔子的名義發(fā)生影響的,在長(zhǎng)期歷史中,廣泛地受到人們的服膺尊崇,激勵(lì)著廣大民眾奮發(fā)前進(jìn)、在困難面前決不屈服,同時(shí)保持著廣闊的胸懷”(《全集》第七卷,第69頁(yè))。
1992年1月27日,張先生在《炎黃傳說(shuō)與民族精神》一文第三節(jié)“何謂民族精神”中認(rèn)為,傳統(tǒng)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因素,而“嚴(yán)格意義的民族精神專(zhuān)指能促進(jìn)民族發(fā)展的積極傳統(tǒng)”,“積極傳統(tǒng)即能促進(jìn)社會(huì)發(fā)展的傳統(tǒng),消極傳統(tǒng)即落后的拖延社會(huì)發(fā)展的種種思想意識(shí)”(《全集》第七卷,第220頁(yè))。張先生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屹立于世界東方五千多年,必有其所以能夠自立的思想基礎(chǔ)。
中華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思想基礎(chǔ),即是中國(guó)文化中的積極傳統(tǒng),即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須滿(mǎn)足兩個(gè)條件,才可以成為民族精神。一是具有廣遠(yuǎn)的影響,為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二是能促進(jìn)社會(huì)的發(fā)展,是推動(dòng)社會(huì)前進(jìn)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必然是文化學(xué)術(shù)中的精粹思想,在歷史上曾經(jīng)具有激勵(lì)人心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稱(chēng)之為民族精神”(《全集》第七卷,第221頁(yè))。
在《炎黃傳說(shuō)與民族精神》第四節(jié)專(zhuān)門(mén)談“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張先生說(shuō)“近幾年來(lái),關(guān)于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我提出一項(xiàng)見(jiàn)解,認(rèn)為《周易大傳》的兩句話(huà)‘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這只是用最簡(jiǎn)括的詞句來(lái)表示民族精神的核心內(nèi)容。這兩句話(huà)有深厚的哲學(xué)基礎(chǔ)和豐富的理論含義,這需要加以解釋。自強(qiáng)不息的哲學(xué)基礎(chǔ)是重視人格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厚德載物的哲學(xué)基礎(chǔ)是重視整體的以和為貴的理論”(《全集》第七卷,第221頁(yè))。從“以人為本”(主體性)來(lái)講自強(qiáng),這是張先生之前沒(méi)有講過(guò)的。
接著張先生又展開(kāi)了更具體的論述,他認(rèn)為“自強(qiáng)就是在德行、知識(shí)、能力各方面不斷提高,從而保持自己的人格尊嚴(yán)。自強(qiáng)觀念包含對(duì)于人的主體性的肯定,包含對(duì)于人的主觀能動(dòng)性的肯定”(《全集》第七卷,第221頁(yè)),“儒家強(qiáng)調(diào)道義之強(qiáng),即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堅(jiān)持原則,不屈不撓”,“‘自強(qiáng)不息’就是堅(jiān)持自己的主體性、努力上進(jìn),決不休止。自強(qiáng)不息的精神亦稱(chēng)為剛健”,“在中國(guó)歷史上,剛健自強(qiáng)的思想起了激勵(lì)人心的偉大作用。特別是在國(guó)家民族遭受外來(lái)侵略的時(shí)候,志士仁人、愛(ài)國(guó)群眾起來(lái)進(jìn)行英勇的斗爭(zhēng),更顯出剛健自強(qiáng)思想的光輝”(《全集》第七卷,第222頁(yè))。
自強(qiáng)不息是積極進(jìn)取的精神,相比之下,厚德載物是一種“博大寬容的精神”,含有“寬柔以教”的意謂,“厚德載物,即待人接物,要具有寬容、寬柔的態(tài)度。既肯定自己的主體性,也承認(rèn)別人的主體性;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嚴(yán),也要承認(rèn)別人的人格尊嚴(yán)。在國(guó)際關(guān)系上,厚德載物的原則表現(xiàn)為和平共處,反對(duì)侵略戰(zhàn)爭(zhēng)。中華民族向來(lái)不主張向外進(jìn)攻,古代建筑的長(zhǎng)城,本是一種防御的工程,這也是中國(guó)文化中重視和平的表現(xiàn)”(《全集》第七卷,第222頁(yè))。
個(gè)人、民族都有努力保持其主體性的獨(dú)立和尊嚴(yán),這是自強(qiáng)不息精神的體現(xiàn),與此同時(shí),還要將心比心,尊重別人的主體性,不能因張揚(yáng)自己的主體性限制、妨礙乃至打壓別人主體性的伸張。張先生此論,與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提倡的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交往理性之說(shuō)有些類(lèi)似。賀來(lái)認(rèn)為,“主體性”是哲學(xué)中一個(gè)十分重大的課題,在20世紀(jì)80年代至90年代,“主體性”觀念在中國(guó)當(dāng)代哲學(xué)的進(jìn)程中產(chǎn)生了十分特殊的作用,對(duì)于推動(dòng)思想解放、觀念變革居功至偉(5)。
在《炎黃傳說(shuō)與民族精神》一文,張先生還指出“‘自強(qiáng)不息’的精神可以說(shuō)是中國(guó)文化與西方文化共同具有的,并非中國(guó)文化的特點(diǎn)。‘厚德載物’的寬容而愛(ài)好和平的精神,卻是中國(guó)文化所獨(dú)有的特點(diǎn)”(《全集》第七卷,第223頁(yè))。這可以看作是對(duì)1986年8月青島講話(huà)認(rèn)為只有中國(guó)才有兼容并包精神、沒(méi)有發(fā)生宗教戰(zhàn)爭(zhēng)觀點(diǎn)的一種發(fā)展。從今天構(gòu)建人類(lèi)命運(yùn)共同體的角度來(lái)看,“厚德載物”、愛(ài)好和平的精神非常重要。就此而言,張先生的這一看法是有前瞻性的。當(dāng)然,這與民族復(fù)興的時(shí)代背景也是分不開(kāi)的。1990年代的中國(guó),政治獨(dú)立,經(jīng)濟(jì)迅猛發(fā)展,這與百年前任人宰割的國(guó)運(yùn)已不可同日而語(yǔ)。
1992年4月12日,在《中國(guó)文化的光輝前途》中,張先生又說(shuō)“‘自強(qiáng)不息’,亦稱(chēng)為‘剛健’即奮發(fā)向上,堅(jiān)強(qiáng)不屈,永遠(yuǎn)前進(jìn),決不停止。‘厚德載物’,是寬厚待人,團(tuán)結(jié)群眾。‘自強(qiáng)不息’表現(xiàn)了奮斗精神,‘厚德載物’表現(xiàn)了寬容精神。我認(rèn)為這是中國(guó)文化的基本精神”(《全集》第七卷,第246頁(yè))。1992年5月3日,張先生在《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中關(guān)于德力、剛?cè)岬恼摖?zhēng)》一文中“自強(qiáng)不息即是剛健精神,厚德載物即是寬柔精神,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表現(xiàn)了剛?cè)岬慕y(tǒng)一”(《全集》第七卷,第253頁(yè))。
1993年2月9日,張先生在《中華民族精神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一文中說(shuō)“自強(qiáng)不息涵蘊(yùn)著主體性的自覺(jué)。厚德載物顯示著以和為貴的兼容精神”(《全集》第七卷,第329頁(yè))。就一個(gè)民族而言,自強(qiáng)不息,強(qiáng)調(diào)民族的獨(dú)立與尊嚴(yán),是愛(ài)國(guó)主義的精神支柱。“厚德載物”,“道并行而不相悖”,體現(xiàn)的包容精神使得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思想主張可以和平相處。
1993年7月7日,張先生在《中國(guó)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中以“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以和為貴”為中華文化的四項(xiàng)基本觀念。顯然,后兩項(xiàng)即是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精神的體現(xiàn),張先生說(shuō)“在古代哲學(xué)中,與剛健自強(qiáng)有密切聯(lián)系的是關(guān)于獨(dú)立意志,獨(dú)立人格和為堅(jiān)持原則可以犧牲個(gè)人生命的思想”“堅(jiān)持自己的人格尊嚴(yán),這是剛健自強(qiáng)的最基本的要求”(《全集》第七卷,第382-383頁(yè))。孔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主張就體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
張先生認(rèn)為“在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中,儒家宣揚(yáng)‘剛健自強(qiáng)’,道家則崇尚‘以柔克剛’,這構(gòu)成中國(guó)文化思想的兩個(gè)方面。儒家學(xué)說(shuō)的影響還是大于道家的影響,在文化思想中長(zhǎng)期占有主導(dǎo)的地位。剛健自強(qiáng)的思想可以說(shuō)是中國(guó)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全集》第七卷,第383頁(yè))。
1994年12月4日,張先生在《愛(ài)國(guó)主義與民族精神》一文中,指出中國(guó)文化的兩大基本精神,“一是剛健自強(qiáng)的進(jìn)取精神,二是以和為貴的寬容精神”(《全集》第七卷,第554頁(yè))。張先生在文中批評(píng)了那種認(rèn)為中國(guó)文化安于現(xiàn)狀、缺乏西方那種積極進(jìn)取精神的觀點(diǎn),他認(rèn)為“在中國(guó)哲學(xué)中,道家固然主張回到自然、反對(duì)進(jìn)取;而占主導(dǎo)地位的儒家則是主張積極有為的”,《易傳》剛健自強(qiáng)的主張“即是能克服一切艱險(xiǎn),這正是積極進(jìn)取的精神”(《全集》第七卷,第554頁(yè))。張先生又說(shuō)“這種積極進(jìn)取精神是與西方文化的基本態(tài)度相互近似的。但是中國(guó)文化宣揚(yáng)一種以和為貴的寬容精神,則與西方迥然不同了”(《全集》第七卷,第554頁(yè))。這里,張先生也強(qiáng)調(diào)了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
1996年2月,張先生在其《全集·自序》中述及生平學(xué)術(shù)時(shí),最后說(shuō)“我提出民族精神的問(wèn)題,認(rèn)為任何一個(gè)文明的民族都有其獨(dú)特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幾千年來(lái)屹立于東方,必有其延續(xù)不絕的民族精神。我提出,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傳》的兩句話(huà)來(lái)表述,即是‘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所謂‘自強(qiáng)不息’即是發(fā)揚(yáng)自覺(jué)性、堅(jiān)持前進(jìn)的精神;所謂‘厚德載物’即是以和為貴、寬容博厚的精神。我認(rèn)為,中國(guó)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稱(chēng)為‘中華精神’。這是中國(guó)文化優(yōu)秀傳統(tǒng)的核心”(《全集》第一卷,第4頁(yè))。
張先生生于1909年,2004年辭世,1985年他提出以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為中華民族核心精神時(shí),已77歲高齡,那么,此后的十多年他一直對(duì)此反復(fù)宣講、闡釋?zhuān)谒枷胛幕鹘缒酥辽鐣?huì)上都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些闡釋看起來(lái)大同小異,實(shí)際上從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他的一些講法也在變化,反映了他對(duì)此問(wèn)題思考的不斷深入。同時(shí),從晚年張先生的學(xué)術(shù)自述來(lái)看,他對(duì)此非常重視,自覺(jué)地將其視為其學(xué)術(shù)的最后一個(gè)重要發(fā)明,是對(duì)民族文化發(fā)展的重要思想貢獻(xiàn),也是其一生學(xué)術(shù)情懷的凝結(jié),充分體現(xiàn)了張先生強(qiáng)烈的學(xué)術(shù)報(bào)國(guó)的愛(ài)國(guó)主義精神。
四、余論
張先生以“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為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這一點(diǎn)在社會(huì)上產(chǎn)生廣泛影響,并被普遍認(rèn)可(6)。張先生講自強(qiáng)不息,強(qiáng)調(diào)其愛(ài)國(guó)主義精神的激揚(yáng),這對(duì)我們今天強(qiáng)調(diào)以愛(ài)國(guó)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有影響的。當(dāng)然,愛(ài)國(guó)主義更多是乾卦自強(qiáng)不息精神的體現(xiàn),強(qiáng)調(diào)的是民族獨(dú)立、民族自強(qiáng),是對(duì)民族精神主體性的彰顯。而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shí)代精神,實(shí)際上也是乾卦精神的體現(xiàn)。
愛(ài)國(guó)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全面來(lái)說(shuō),講民族精神,也應(yīng)包括坤卦的包容精神、和平精神。我們今天講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結(jié)合乾坤兩卦的精神來(lái)說(shuō),連續(xù)性是講生生不息,它與生生日新的創(chuàng)新性,可以歸為乾卦自強(qiáng)不息的精神,而和平性、包容性可以歸為坤卦厚德載物的精神,統(tǒng)一性居中可以說(shuō)是太極大中之道。
民族精神與時(shí)代精神是辯證統(tǒng)一的。民族精神是一個(gè)民族恒定的價(jià)值觀,有永恒性,貫穿過(guò)去、現(xiàn)在、未來(lái),民族精神在每一個(gè)時(shí)代又有著具體的表現(xiàn),時(shí)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當(dāng)下綻放。“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是民族精神的很好概況,就今天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而言,如果繼續(xù)結(jié)合《周易·大象傳》來(lái)講,實(shí)際上可以加上咸卦“以虛受人”,以及恒卦“立不易方”。
乾坤為《周易》上經(jīng)的頭兩卦,咸恒為《周易》下經(jīng)的頭兩卦,“以虛受人”與“厚德載物”的精神類(lèi)似,但又有所不同,它更強(qiáng)調(diào)虛懷若谷,主動(dòng)學(xué)習(xí)汲取別人的長(zhǎng)處,與外界發(fā)生真切、篤實(shí)、暢通、向上的內(nèi)外感應(yīng)與信息能量交換;“立不易方”與“自強(qiáng)不息”的精神相呼應(yīng),但又有所不同,它更強(qiáng)調(diào)自己的原則性、立場(chǎng)性。在新時(shí)代錯(cuò)綜復(fù)雜、風(fēng)云變幻的國(guó)際關(guān)系中,《周易·大象傳》“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以虛受人”“立不易方”,以此作為民族精神的時(shí)代新表述,可以與以愛(ài)國(guó)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shí)代精神相呼應(yīng),為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人類(lèi)命運(yùn)共同體的建構(gòu)提供精神力量。
注釋?zhuān)?/strong>
(1)劉綱紀(jì):《略論中國(guó)民族精神》,《武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85年第1期。
(2)謝幼田:《中國(guó)民族精神探析》,《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1986年第2期。
(3)遲成勇:《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國(guó)學(xué)大師張岱年的民族精神觀的解讀》,《南京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6年第1期。
(4)《張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5-196頁(yè)。
(5)參見(jiàn)賀來(lái):《“主體性”的當(dāng)代哲學(xué)視域》,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
(6)張先生本人之人格也是“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精神的寫(xiě)照,陳來(lái)指出“張先生一向謙和待人,有求必應(yīng),他既是誨人不倦的導(dǎo)師,又是忠厚寬和的長(zhǎng)者。‘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正是他自己從事學(xué)術(shù)工作和待人處世的寫(xiě)照”(陳來(lái):《張岱年: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的哲學(xué)家》,《燕園問(wèn)學(xué)記》,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50頁(yè))。
【編輯:】
文章、圖片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quán)請(qǐng)聯(lián)系刪除- 孔子博物館圓滿(mǎn)完成國(guó)慶假期開(kāi)放工作
- 奏響文旅“詩(shī)與遠(yuǎn)方”的新樂(lè)章
- 以堅(jiān)定文化自信走向未——寫(xiě)在故宮博物院建院百年之際
- 國(guó)慶中秋假期各地豐富文旅產(chǎn)品供給,滿(mǎn)足個(gè)性化需求——深度體驗(yàn) 文化入心
- 讓優(yōu)質(zhì)文化資源直達(dá)群眾“家門(mén)口”
- 今日中秋,天涯共此時(shí)!
- 孔子博物館圓滿(mǎn)完成國(guó)慶假期開(kāi)放工作
- 中俄孔子文化書(shū)畫(huà)展在莫斯科成功舉辦
- 奏響文旅“詩(shī)與遠(yuǎn)方”的新樂(lè)章
- 奏響文旅“詩(shī)與遠(yuǎn)方”的新樂(lè)章
- 雙節(jié)相遇!“人文”與“經(jīng)濟(jì)”輝映共生
- 以堅(jiān)定文化自信走向未——寫(xiě)在故宮博物院建院百年之際